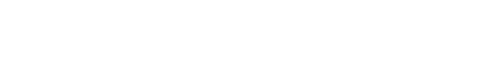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6年第4期,作者:虞云国,原题为:《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宋朝》
核心提示:宋朝士大夫官僚确享有一定的言论自由,那是相对其它专制王朝而言,但即便宋朝也仅限于政治生态良性运作期。南渡以后,政治生态明显恶化,秦桧在宋高宗的默认下,屡兴文字狱置反对派于死地;韩侂胄以“伪学逆党”倾陷政敌,厉禁道学与道学派,都是众所周知的。误读者不论前提与时段,全面判定宋朝是“没有思想禁区”与“没有文字狱的时代”,显见是大谬不然的。
大致以中唐为分界,中国历史在政治制度、经济构成、社会关系与思想文化诸领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两宋存世期间,外部环境基本处于北方强邻压境的态势下,先是1127年北宋亡于金朝,南宋被迫立国东南;1279年在与蒙元军队的崖山决战中,南宋最终覆灭。我们站在当下,倘欲理性地评价宋代,必先对两宋史作一概览。
【两宋大势】
公元960年,袭用五代武将拥兵问鼎的故伎,宋太祖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宋朝。开国后,由他亲手擘画,再经其弟宋太宗完善,形成了一系列制度规范,称为“祖宗家法”,为中央集权的君主官僚政体开出了新局面。他与宋太宗推行“先南后北”战略,借助战争或和平的手段,至979年最终平定了南北割据政权,完成了中原王朝的相对统一。
自五代后晋起,作为中原王朝的稳固屏障,长城防线已南北易手转归辽朝掌控,宋太宗两度试图夺回,在雍熙北伐中终遭毁灭性打击,导致宋朝对北邻游牧政权产生了根深蒂固的畏惧心理,转而确立了守内虚外的基本国策。1005年初,宋朝遏制住辽军南下的势头,订立了“澶渊之盟”,以岁币为双方换来了长期和平。在其后与西夏的较量中,宋朝再处下风,仍以“岁赐”换和平收场。这种外交定式,也影响了南宋与金、蒙的折冲。
经过立国前期恢复,自北宋中期起,社会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手工业领域出现了所谓“煤铁革命”,铁产量与冶炼术均居世界之首,煤的采用促成了工艺技术与城市生活的进步,手工业分工的细密化与专业化程度大为提高。冶铁技术的改进促成了农具革新,梯田、圩田、湖田等大量开垦,全国耕田额大幅度增加,传统农业发生了重大变革。
城市也一改前代隔绝的格局,打通了商业区(市)与居住区(坊)的坊墙,取消了城郭区别与宵禁制度,实行开放式管理。这就促进了传统的政治性城市向经济性城市的转化,工商贸易与文化消费的成分大为增强。城镇化速度随之加快,开封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大中城市外围构筑了以县镇为拱卫的网络,市集则星罗棋布于网络末梢。城镇网络为城市社会的繁荣与市民文化的勃兴提供了平台,商品经济也随之飞跃。不仅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甚至文化消费,也都进入了流通领域,自然经济开始向商品经济转型。11世纪初叶发行的“交子”,作为最早的纸币,标志着商品经济的总体水平。
但宋初以来崇文抑武、守内虚外的国策,致使“冗兵”“冗官”与“冗费”积重难返,政府财政陷入困局。“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政策,也使小农经济往往濒临贫弱无助的破产境地,群体性兵变与民变时有发生。为解决这些问题,范仲淹促成了“庆历新政”,却以夭折而告终。宋神宗重用王安石,把统治阶层的自改革推向高潮。以富国强兵为目的,以理财为重心,王安石推出了一系列新法,也取得了相当成效。但在应对改革力度与社会承受力、动机与效果、条文与执行、立法与用人等关系上,变法运动存在着一定的偏差,遭到不同政见官员与既得利益集团的激烈反对。在适当微调、巩固新法后,宋神宗着手中枢决策和职官制度的改革,进而试图解决西北问题,但两攻西夏均告失利,抑郁而死。宋哲宗在位,先是“更化”派全面否定变法,继而“绍述”派继续推进新法,双方党同伐异,朝局反复折腾。
宋徽宗继位,借新法之名,行聚敛之实,变法彻底变质;同时全面放逐异见派官僚,以期与蔡京等代理人独掌中央控制权。到其后期,一方面人口突破一亿大关,社会经济跃上新高度,城市繁荣尤其令人瞩目,形象展现在《清明上河图》中;但另一方面朝政日趋腐败,盘剥变本加厉,深层次社会矛盾逐渐凸显。宋朝决策者无视繁荣表象下的内在危机,与勃兴的金朝结盟夹击辽朝,却在军事行动中尽露马脚。金朝随即兵临东京城下,宋徽宗仓皇让位给宋钦宗。1127年发生靖康之变,北宋转瞬间崩溃式灭亡。
就在徽、钦父子被掳北上当年,宋高宗以徽宗第九子身份即位南京(今河南商丘),成为南宋第一代君主。面对金军的凌厉攻势,他唯求自保,一路南撤。经南渡将领数年安内攘外,南宋方与金朝形成对峙之势,以临安府(今浙江杭州)为行都,确立了偏安之局。但宋高宗一味乞和,在岳飞大军一再获捷的形势下,强令撤兵,向金朝贡币割地称臣,签订了屈辱的“绍兴和议”。为外交内政的双重维稳,宋高宗与代理人秦桧大权独揽,严酷镇压异见派官僚与在野士大夫,政局急遽转向专制甚至独裁,南宋政治进入最黑暗时期。但宋金和议终究是南北地缘政治相对平衡的产物,其后虽有金朝的正隆南侵,宋朝的隆兴北伐与开禧北伐,但任何一方都不足以打破平衡态势。几次短暂的兵戎相见,也未能逆转双方和平共处的总体格局。
宋孝宗在位,虽异论相搅以君权独断,但朝政相对宽松,言路相对自由,在北伐无望后致力于内部发展,思想文化与社会经济在北宋的轨辙上继续前行,迎来了新的繁荣。各学派知名学者主持书院,传道讲学,切磋论辩,迎来了宋学第二高峰期,由朱熹集大成的理学最终成为宋学的主流。
中国历史上的经济重心自安史之乱起由北向南倾斜,到北宋末年,南方耕地与人口数均占全国2/3以上,经济重心南移的大局已形成。宋室南渡,北方人口再次大规模南徙,经济重心南移的格局最终不可逆转。凭借造船技术的进步与航海罗盘的使用,以经济实力为强大后盾,宋朝大力开拓海上贸易,外贸地区、规模与税收远逾前代,自南宋起迎来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黄金时代。城市经济更加发展,市民文化日臻成熟,南宋临安的繁盛程度超过了北宋开封。
宋宁宗即位后,大臣韩侂胄为排击政敌,专擅朝政,以“伪学逆党”的污名迫害理学派官僚及其同情者,政治生态再度恶化。其后三朝,君弱臣强,专制模式呈现出权相专政的特殊形态,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等先后专权。统治集团愈加腐败,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滥发纸币,财匮民困,强行公田,怨声载道,政局暗乱不可逆转。
随着蒙古崛起,南宋趁蒙古南侵金朝之机,中止与金的和约,双方重开战端。宋理宗亲政,在联蒙灭金后随即进取河洛,受挫后即与蒙古进入战争状态,抗衡长达四十余年。宋度宗时,贾似道主政,对决定大局的襄樊之战失于驰援,终致陷落,元朝大军得以沿江东下,1276年进围临安城下,宋恭帝投降。朝臣先后拥立幼君帝昰与帝昺,辗转闽粤沿海,继续抗元活动。1279年,流亡政权连同其舰队在崖山决战中全军覆没,标志着南宋最终灭亡。
【宋朝的珍贵遗产】
严复说过:“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玩味其言,宋朝虽已远去,却是造就今日的重要朝代;宋朝的遗产不胜枚举,但事关政俗人心而值得究心盘点的,显然应该聚焦于政治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层面。
宋朝的政治文化遗产主要体现在制度设计与统治思想上。
先说制度设计。宋朝确立文官体制,抑制武将势力。宋朝立国后,在军事制度上创设了枢密院、三衙的新体制。中央禁军分为马军司、步军司与殿前司,三衙鼎立,互相牵制,改变过去由一将独领的做法,三衙主帅只有统兵权,没有发兵权。与此同时,另设枢密院作为最高军事机构,长官一般由文臣担任,只有发兵权,而无统兵权。每有征战,皇帝亲自命将,所命主将未必都是三衙之帅。宋朝实行强干弱枝、内外相制的方针。无论数量还是质量,京师禁军都比地方禁军雄厚精良,旨在拱卫京师,弱化地方,此即强干弱枝。在禁军布防上,则一半驻守京城,一半分驻外地,合京城禁军足以对付外地一处的禁军,合外地禁军也足以对付驻守京城的禁军,不至于酿成外患内乱,此即内外相制。这些削夺兵权、改革兵制的措施,有效保证了军队的稳定,彻底终结了晚唐五代以来武人乱政的动荡局面。
为防范相权独大,威胁君权,宋朝采取了三项措施。首先,把最高行政机构分为中书门下与枢密院,把原属宰相的那部分军事权力划给了枢密院。其次,增设参知政事作为副相,防范宰相专擅。另外,增设三司总理全国财政,把财权也从宰相手里分割出去。
在地方政权上,派遣文官主政州县,直接对皇帝负责,另设通判掣肘州府长官。在州府之上,派驻代表中央的路级机构,主要有漕司、宪司、仓司和帅司。前三者分别主管一路的财赋、司法与赈济,同负监察一路州县官的职责,故统称“监司”。帅司专掌一路军事和治安。作为路级机构,四司既各专其职,又相互督察,这种互相牵制的权力结构,看似叠床架屋,却使任何地方大员都不能专权独断,更不可能出现类似藩镇割据那样尾大不掉的祸患。
宋朝在政治制度上的顶层设计,作为影响深远的政治遗产,为后代所继承。直至近代以前的帝制时代,除却王朝鼎革之际,从未再上演过皇权倾覆与地方割据的大乱局面,说其泽被后世,也是绝不夸张的。
再说统治思想。纵观宋朝制度,其顶层设计之完善与统治思想之进步是相互促进,同步展开的。宋代的统治思想已达到了这样的共识:“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后天下之大公始立。”在确立重用文臣、抑制武将基本国策的同时,开国者特立不杀士大夫和言事官戒誓,作为后世君主必须恪守的制度保障。这种政治宽容度,在中国帝制时代堪称空前绝后,故而宋代朝政在中国历代王朝中称得上是最开明与宽容的。
宋朝士大夫独立人格之养成,当然有社会变动的深层原因,但最高统治者的政策保护与思想导向,其作用不可忽视。尤其对于承担权力监察功能的台谏言事官,宋朝君主大都以“崇奖台谏”“不罪言者”相标榜,“借以弹击之权,养其敢言之气”。正是最高统治者能够“容受谠言,养成臣下刚劲之气”,促使士大夫官僚“所以自待者愈不敢轻,上下交相待,而人才日以盛”,他们才得以相对充分地议政论政,实现其政治抱负。
宋朝精神文化遗产的核心内容,是指当时那些出新前代却影响至今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与民族性格。宋学不仅是学术思潮,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对宋代以后迄于今日的民族素质与价值信仰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举其荦荦大者,略有以下诸端。
其一,平等意识。唐宋社会转型,开启了科举公平竞争的闸门,包括工商业者在内的各阶层子弟都有可能登第入仕。整个官僚队伍主要出自科场的选拔,他们虽有等级高低,但“比肩事主”,法律身份上是平等的。地主阶级已无“士庶之别”,地权开始以经济手段频繁转移,地主、自耕农与佃户都可能因土地得失而地位浮沉。不仅仅耕地租佃,相对平等的契约关系也开始进入许多经济活动。农民与手工业者开始拥有迁徙权与流动权,促进了各阶层间的横向流动与上下流动。所有这些变化,催生了人们对平等的朦胧向往。宋学家倡导“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就是强调这种平等观。在社会上,以农为本、工商为末的传统思想受到挑战,出现了士农工商四民平等的观念(这在近代公民意识出现前不啻是身份观念的革命)。平等观也投射在起义农民的纲领口号上。王小波的“均贫富”,方腊的“法平等”,钟相的“等贵贱”,都表达出对社会平等的强烈诉求。相对前代,这种平等意识是新因素,但与近代平等观仍有本质区别。
其二,兼容精神。宋朝政治氛围相对宽松,兼容精神遂应运而生。宋学在其创立形成期秉持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颇具怀疑精神与创新活力。观宋学的两大高峰期,“学统四起”“自出议论”,却颇能宽容并存,客观肯定别派可取处。与此同时,佛门在学理上融合儒道,道教从儒佛中汲取养分,而最高统治者也以兼容精神处理宗教关系,三教和平共处成为宋朝常态。至于士庶日常行事,往往儒、佛、道并行不悖而同处杂陈。在雅俗文化的互融共处上,整个社会表现得相当宽容。正是在兼容并蓄中,士农工商不断吸收、借鉴、融合其它异质文化,创造出璀璨辉煌的文化遗产并影响至今。
其三,经世理念。宋代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入世型文化,讲究履践,强调经世,从根本上关注百姓怎样生存发展、国家如何安宁强盛,体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淑世情怀。唐宋转型后,经科举制的有力推动,一个士大夫官僚阶层迅速崛起。他们中的精英分子自许是天下安危、生民利病的实际担当者,向皇帝发出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吁请,展现出迥异于前代士人的自觉意识。即以理学强调“内圣外王之道”而论,就是旨在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内圣”功夫,最终落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道上。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号召,都是这种理念情怀的经典表述。
其四,名节操守。晚唐五代以降,忠义廉耻扫地以尽。新儒学重建过程中,表彰名节操守尤其不遗余力,至北宋中叶已“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名节操守敦促优秀的士大夫官僚“不枉道以求进”,自觉信奉“刑赏为一时之荣辱,而其权在时君;名义为万世之荣辱,而其权在清议”,将当世与后代对自己的评价视为高过赏罚、超越生命的永恒价值。
当然,宋朝的遗产也有消极因素,而且利弊得失往往藤缠葛绕共生在一起。
就政治遗产而言,其制度设计固然确保了君主集权,根绝了分裂割据,但时时处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在军事上,各自为政、缺乏协调、难以统筹等弊病如影相随,严重削弱了军队战斗力。在行政上,政出多门、官员冗滥、效率低下等现象也司空见惯。于是,强敌压境、时局纷扰之时,缺少活力、短于应对也就在所难免。
就精神遗产而言,作为精神文化内核的新儒学确为时代注入过许多新元素,但随着外部环境的压力与内部专制的强化,自宋理宗起,理学作为宋学主流获得尊崇,升为官学,创立期的兼容精神日渐泯灭,而“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教条经过后代的发酵,最终成为明清专制帝国控制官僚、驯服百姓的精神桎梏。
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理性区分宋朝遗产中的新生儿与洗澡水,全单照收与一起泼掉的做法都不足取。
【关于宋朝的几种误读】
宋朝立国年代长,史料存世数量大,未经全面占有,缺乏深入研究,仅凭个别记载,便下全局判断,难免会出现失误。以下几种误读,当前亟须纠偏。
第一,过度美化宋朝。
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宋朝确实出现了新气象,但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毕竟未脱君主专制与地主经济的大框架。误读者往往抽离大前提,不分时段区域,将若干新元素绝对化、普遍化与一贯化,进而作为过度夸饰的支撑性依据,其结果必然有违历史事实。
先说社会经济。有误读者将宋朝说成是农民“自由、快乐地生活的朝代”,显然有失偏颇。宋朝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虽有改善,但官府代表国家对其控制与盘剥并未放松;他们的生活在总体水平上尽管比前代有所提高,但总不能将宋朝美化成“广大民众的黄金时代”。
次说言论环境。宋朝士大夫官僚确享有一定的言论自由,那是相对其它专制王朝而言,但即便宋朝也仅限于政治生态良性运作期。南渡以后,政治生态明显恶化,秦桧在宋高宗的默认下,屡兴文字狱置反对派于死地;韩侂胄以“伪学逆党”倾陷政敌,厉禁道学与道学派,都是众所周知的。误读者不论前提与时段,全面判定宋朝是“没有思想禁区”与“没有文字狱的时代”,显见是大谬不然的。
再说士风名节。新儒学确有砥砺人心之功,也出现了范仲淹、包拯、文天祥等一批士大夫精英。精英有榜样的力量,但士风从来随政风互动。在良好政风下,例如北宋庆历、嘉祐时,士风相对振作,操守自然高扬。政局一旦污浊,虽仍有少数士大夫不为所屈,但秦桧、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专政时,士风窳败,斯文扫地,何来风骨气节可言,而这些权臣与麇集其麾下者,十之八九不都是士大夫官僚吗?足见笼统断言宋朝是“君子时代”,无疑也是误读。
第二,无关中国模式。
观过度美化宋朝者,大多是历史爱好者以偏概全的认知性误读;但也有极度美化者将宋朝政治等同于当下的中国模式。如前所述,宋朝在政治文明上有着长足的进步,但其所有进步都是相对的,而且是在专制政体下展开运作的;皇帝仍是国家最高决策者,祖宗家法下所有顶层设计无不服务于君主专制集权。把宋朝政治误读为现今中国模式的根本失误,就在于有意无意地忽视君主专制这个大制度,而处心积虑地美化某些小制度。
比如,宋神宗与宋哲宗时期有新旧党争,有人将其说成“以王安石为偶像的改革党与以司马光为偶像的保守党两党轮流执政”,用以论证宋朝已“有共和的因素”。这种说法把古代帝制下两党轮流辅政与近代意义上两党轮流执政混为一谈。一字之差的症结,旨在抹杀民主共和与君主专制的本质差异。
宋孝宗与宋理宗都以旁支宗室而入继皇位,有人将其曲解为政治上“‘谁都可以当皇帝’的开放性”。纵观中国历代王朝,因君主绝嗣而旁支承统的权变做法,并非宋朝独有,若将其美化成宋朝已具“皇权开放的观念”,实在匪夷所思。君不见,皇权依旧在赵姓皇帝后代中私相授受,“皇权开放”从何谈起。
有人把宋朝对皇权及其决策程序的相对制约,解读为“皇权成为最高公权力的象征”。殊不知宋朝这种相对制约,最终必须以皇帝自觉接受权力制衡为前提。这也决定了代表皇权的宋朝皇帝不可能像近代立宪制那样彻底虚君化,也就谈不上宋朝“以制度保障了国家公权力最大限度地属于全社会”。
更有甚者,有人声称:“令全世界疑惑的‘中国模式’,其实就是宋朝政治的核心理念:超越利益集团。”说宋朝国家政权已经超越利益集团,是“一个高于各个利益集团的存在”,这不仅缺乏关于国家权力的政治学常识,更经不起宋朝政治诸多史实的有力否证(见2014年1月19日《上海书评》拙文《宋朝政治难为现实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