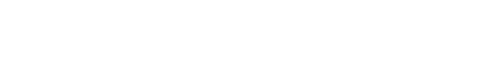2015年09月17日 社会科学报
星空体育·(china)官方网站 田洪敏
1995年纽约“法拉尔 、斯特劳斯和吉罗克斯”出版社发行布罗茨基散文集《悲伤与理智》 ,次年该书在英国出版;2000年俄罗斯普希金基金会出版了它的俄文版;2015年文字变成漂流瓶,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发行中译本。该书收录了布罗茨基1986-1995年的散文和杂谈。在21篇文章中,其中19篇是用英文写作, 2篇用俄文完成。
开篇《战利品》中布罗茨基回忆了自己的苏联生活。其中谈到对于一位美国影星的印象:“我在许多年间一直试图模仿他高高抬起的下巴和能独自上挑的左眉,后一个动作我始终未能模仿成功。”——不过,前一个动作却成为莫斯科布罗茨基雕像的灵感来源。2011年5月30日由俄罗斯著名雕塑家弗兰古里安设计的布罗茨基雕像在莫斯科落成。作品前后耗时七年,这其中除了艺术上的斟酌,也包括协调各种市政关系,比如如何迁走生意兴隆的商家,解决位于雕像地下的下水管道问题等等。雕像坐落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对面,这一选址多少引起了人们的议论。但是当人们意识到雕像的完成是弗兰古里安一己之力,这其中包括巨大的财力支出,这是雕塑家“送给莫斯科的礼物”;同时人们想起布罗茨基正是通过美国人签发的一张过境签证告别了苏联,过分自尊的指摘者终于默认了布罗茨基就应该“站”在美国使馆对面。雕塑采用平板铜质材料,底座为花岗石——彼得堡涅瓦河畔也是这样的花岗石。雕像中的布罗茨基面朝美国大使馆,仰望天空,显得强大而自信,当然他的表情里一定不会缺少俄罗斯民间文学般的诙谐与幽默。他的背后则是看不清面目的两组雕像,按照弗兰古里安的解释,雕像群是布罗茨基的朋友或者敌人。布罗茨基最终成为了一个美国公民,不过人们都称呼他为“俄语诗人”,诗人自己也这样认为。
当然,布罗茨基的故乡并非莫斯科,他1940年出生在列宁格勒(彼得堡),1972年离开苏联,并于1977年加入美国国籍。十年之后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96年布罗茨基去世,最后的安息地是威尼斯圣米歇尔墓地。布罗茨基曾经收到一个姑娘送给他的一套威尼斯风光明信片。“那些画面所呈现的色调和哀伤氛围与我的故乡十分相近”——布罗茨基后来如此写道。这多少可以解释布罗茨基为什么喜欢威尼斯,因为它和彼得堡总有些亲近的地方。
今天,人们在世界各地朗读布罗茨基的诗,不仅是在彼得堡或者纽约,也包括上海。这或许因为布罗茨基对于中国的感性认识:“因为我的父亲是在关东军溃败之后于上海找到这些唱片的。”( 《悲伤与理智》之《战利品》 )2015年春季我惊讶地发现在上海外滩的一个老式酒吧里,人们用绛红色天鹅绒窗帘遮蔽住白日光线,在灯光摇曳下朗诵布罗茨基的诗歌。然后朗读者开始争论是应该用古希腊般工整精致的语调还是应该用工业时代的铿锵有力来阅读布罗茨基,因为据说布罗茨基自己的声音十分高亢,这特别表现在他演讲的时候。这些回忆与真实世界之间的彼此抗衡增加了诗歌的神秘主义特质。这使得我想起了大约十年前在彼得堡,和认识的俄罗斯朋友在夏园散步。他突然说,普希金也曾经在这里散步——我虽然大起疑心却也深信不疑,因为这种情境多少是带有一些暗示的:如果我们愿意,从今天出发到达过去将成为一种可能,而诗歌便是到达过去的坦途。是的,普希金曾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每天早晨,我都穿着睡袍和拖鞋,越过那座桥,到夏园散步,整个夏园都是我的果园……” 同样,带着对于故乡彼得堡的复杂情绪布罗茨基写道: 我出生在波罗的海的彼岸(я родился и вырос в балтийских болотах),这句话翻译为中文很动听,因为“彼岸”。其实这是一句在俄文中应该带着降调去朗读的诗句,因为它的最后一个单词是带有重音、复数意义上的“沼泽地”——彼得堡就是在一片沼泽地上建立起来的。沼泽地带来的是下沉的情绪,所以布罗茨基一直深陷于彼得堡诗歌传统中。这个彼得堡诗歌传统包括阿赫玛托娃和曼德尔施塔姆,这些诗人和奥登、哈代、里尔克、弗罗斯特等诗人一起构成了布罗茨基的诗歌世界。
所以,散文集《悲伤与理智》是一部谈论诗歌的书。虽然也有诗人对于自己苏联生活的回忆或者反刍,但是它从来没有成为言说的中心。喜欢精神分析的评论者一定认为,这本书该成为布罗茨基流亡生活的脚本,为什么不呢?试图厘清存在于作家自身经历之间相互纠缠的线索是很多文学研究者的癖好,而布罗茨基的人生恰好迎合了这种蒙太奇幻境。比如他是个犹太裔作家,出生在二战时期的列宁格勒,青少年时期辍学、打零工,甚至在一次勘探中险些丧命;他在法庭上大谈诗歌,他用余生成就了 “流亡作家”的称号。诗人去世之前,曾经的“苏联”早已经成为“俄罗斯”,布罗茨基却没有再回到他的彼得堡。为什么不顺着这样一条孤独的路径“成为一个悲伤的牺牲者”,为世界举起祈祷的蜡烛?这多少还是会让读者有些踏空的感觉。事实上,把自己放在一个牺牲者的位置上从来没有成为布罗茨基的愿望,布罗茨基认为, “ 在真理的天平上,想象力的分量就等于并且时而大于现实”,而且“用这个(流亡)满含悲伤的字眼去称呼接下来的生活,就显得就过于舒服又过于自在了。”在这一点上,他不是一个俄罗斯人,也不是一个美国人。
从1972年开始布罗茨基开始积极的散文创作,这项工作直到他去世才不得不停止下来。他第一次来到英语世界,看到路边树立的牌子上写道:BED AND BREAKFAST——“我认识这几个单词,可是却幸运地不解其意,因为其中没有动词”。( 《悲伤与理智》之《悼斯蒂芬•斯彭德》 )后来他用英文写作散文并且被喜欢热闹的西方人推为“英语世界第一散文”,他已然使用了很多“没有动词”的英文。诗歌的语言在散文中以一连串的停顿和并列呈现出来,这多少有些断弦的感觉,这是诗歌的声音和调性。从这个意义上看布罗茨基当然是优秀的文体实验师,让诗歌轻易地“颠覆”了散文。
说布罗茨基的散文是诗体散文并非是因为他的文字有多少成分是合仄押韵的,又有多少成分是浅吟低唱,这是因为我们想起了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根尼•奥涅金》 ,诗歌进入小说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帕斯捷尔纳克,伟大的英国作家哈代,当然我们也因此怀念伟大的中国作家曹雪芹。既然如此,我们也就不必讶异一个诗人为什么要写一写散文,这本身就是世界文学传统的一部分。
另外一位美国作家,俄罗斯人纳博科夫曾经警告他的读者,如果要读懂《安娜•卡列尼娜》 ,必须能够想象19世纪中叶一列从莫斯科开往彼得堡的火车是什么样子;如此,如果要读懂布罗茨基是否可以要求今天的读者至少可以想象波罗的海彼岸的彼得堡是什么样子呢。布罗茨基喜欢的彼得堡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说: 诗歌就是对于世界的眷恋。而九月的彼得堡本身就是一句诗:夜已尽,天未白。恰好适合阅读布罗茨基的《悲伤与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