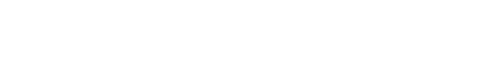| ||
来源:东方早报 2015年4月28日
吴俊范
众所周知,近代以来的上海存在大量的棚户区和居住在其中的城市贫困人口,那么,棚户区是否就是形塑上海“贫困文化”的土壤?上海普通市民中普遍存在的以棚户区为参照物的“住房贫困”心态,是否构成刘易斯所谓贫民窟的贫困文化?本文将围绕这一问题从历史学的角度加以探讨。
民国时期的“住房贫困”情结
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城市社会环境复杂,局势动荡,外地人口急遽涌入,住房成为最紧缺的资源,对住房的占有能力一度成为人们社会地位和身份的标签。花园洋房、新式里弄、旧式里弄、平房、棚户区等不同层级的居住社区,在人们的意识中分别代表着不同社会阶层的分异,住在什么样的社区、住什么档次的房屋,住多大的面积、与哪些人为邻,往往就是一个人的身份名片。这种大都市所特有的社会现实,在市民意识中逐渐促成了颇具上海地域特色的“住房情结”,1930年代后出现的“房荒”,又使这种心态更加牢固。
在这种以住房论贫富的文化氛围中,对不同社会阶层住房状况的关注,成为文化精英社会责任感的一部分,这种责任感又源源不断地体现在各种社会调查报告、报刊或者文学作品中。其中,对占据总人口比例绝大份额的劳动阶层、无房阶层的居住条件的同情和期望改善的呼吁,表现得尤为突出。1926年有朱懋澄《调查上海工人住屋及社会情形记略》出版,他本人指出做此次调查的理由是:“上海实际劳动社会人口总数,约为一百十二万五千人,约占全埠人口百分之七十,是故当吾人研究劳动阶级之情形时,是即研究全城百分之七十之居民之生活状况,是即研究近代之生活秩序也。”由于一般劳动者占城市总人口的比例之大,所以作者潜意识里是将劳动者的居住条件作为体现整个城市生活秩序的一个重要指标,也可见在当时城市的文化心态中,与居住相关的心态所占的重要分量。
上海工人的居住空间,虽然事实上并不仅仅集中在条件最差的棚户区,有些居住在石库门房屋或者平房内,但他们的住处却具有十分明显的共同特征,即“异常拥挤”。正因为拥挤,卫生条件也差,“上海工人住屋的空气和光线是不充裕的,草棚又是其中最不充裕的了”。从景观特征和人口的密集程度来看,将这些贫困人口的住处统称为棚户区似乎也并不为过。
1940年代上海爆发的“房荒”,更成为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1948年3月8日《申报》一篇报道的标题非常醒目:“随房荒应运而生,二房东成时代宠儿——一间过街楼索价八千万,房屋掮客犹如雨后春笋”。而这种对二房东的谴责,只不过是日益加剧的住房贫困问题的一种映射,其背后的社会现实是大量存在的贫困人口和无房阶层,以及密集分布的棚户区。随着内战局势的发展,难民的涌入使整座城市的棚户区问题和贫富悬殊的文化意象更加突出。
劳动大众住房的缺乏和居住环境的严峻,也成为文学、绘画等艺术作品极力表现的对象。例如1947年中国图书杂志公司发行的《上海漫画》中有一幅,画的是一口棺材,一个穿长袍马褂的男人躬伏在棺材中,奋力顶着沉重的棺材盖,口中发出愤怒的呼声:“上海房荒严重有逼人住入此中之势”。既然穿长袍的中产阶级居住状况已经困窘若此,更何况处于底层的广大劳动力、无业者或者工人!
因此民国时期上海人的精神世界普遍存在一种“住房情结”,即全社会对住房困难的普遍的、持续的关注和忧虑心态,这种焦虑意识不仅存在于享有话语权的知识精英阶层的意识中,同时更存在于缺乏话语权的普通市民尤其是社会底层的心态中,只不过一个可能是住房窘态的旁观者,一个却深陷其中,但他们都是住房贫困环境的亲身经历者。在这种焦虑意识的背后,是极其严峻的整体居住环境低下、贫富两极分化这一社会现实,是上海大都市化过程中客观存在而又极具聚焦性的一个社会问题。
“住房贫困”心态的延续与累积
民国时期的“住房贫困”问题,因其真实、客观,波及面广,具有强烈的心灵冲击力,因此这种情结作为一种社会共同记忆,十分自然地延续下去,并在新的历史阶段叠加进更加丰富的内容。
建国后最为典型地揭示旧上海民众内心“住房情结”的文艺作品,是1952年产生的滑稽戏剧本《七十二家房客》,该剧由于直击旧上海住房贫困的要害,贴近普通市民的真实生活,公演后一度引起很大轰动。剧本以1947年前后上海城市为创作背景,入木三分地刻画了社会底层三教九流的住房窘态。其中对故事场景的描写:“上海某弄堂一幢三上三下的旧式石库门房屋,破烂、潮湿,白鸽笼似的房间,一间挨着一间,挤得没有一丝空隙”,具有代表社会下层居住环境的典型意义。其中塑造的人物均系社会底层,包括流氓炳根、二房东的养女阿香、伪警察三六九、医术并不高明的绍兴人金医生、卖梨膏糖的杜福林及其妻子、来自苏北的小皮匠、一大把年纪还要为生计苦苦奔波的老裁缝及其妻子、洗衣为生的小宁波及其妻子、卖大饼的老山东及其妻子、卖香烟的杨老头、末流舞女韩师母等。《七十二家房客》在艺术话语层面上或许把现实中普通市民的住房困难有所夸大,但仍不失为一部以居住景观来诠释上海文化深层性格的优秀作品,以致今天“七十二家房客心态”(指因居住空间局限而形成的个人性格的自卑、市侩气和自私心理)成为上海弄堂文化的代名词。这部作品描写的是解放前的上海社会,但出版、演出的时间却是建国初期1950-1960年代,且一经公演便受到民众广泛接受和欢迎,这本身就说明,无论是作品的创作者还是广大受众,其意识深处某些固有的、真实的社会记忆和心态认知(哪怕是负面的、伤痛的),并不会因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消失,相反可能一遇到与之契合的外部环境,就得以淋漓尽致地再现和复活。
上海城市的住房问题在建国后依然严峻,这是久已形成的住房贫困心态得以延续的现实基础。虽然政府紧抓“工人新村”建设,致力于全面改善普通劳动者的居住条件,但毕竟历史积淀过于厚重,当时能够搬进新公房的毕竟是少数,多数人仍蜗居在拥挤的旧弄堂或局促的棚户区内。可以说,建国初期住房困难仍然是现实中的热点问题和民众内心世界的伤痛。
“住房贫困”心态并非棚户区的贫困文化
刘易斯认为,贫困文化无疑应当存在于城市贫困社区,而这种社区的居民有着明确的社区和领土意识,他们有着明确的贫穷身份感、对未来的绝望感以及与周边社区的隔离感。以美国许多城市的黑人社区为例,居住其中的几乎是清一色的黑人,具有单一的族群性,在物质空间方面他们是被隔离的,受到中产阶级、白人和新教徒的歧视,在居住、读书、工作、教堂、娱乐和社会生活等方面都是被隔离的状态。这些因素加深了他们的自卑感,某种程度上也加深了他们对权威阶层和主流社会的敌意。刘易斯对纽约波多黎各人社区的研究也显示了相似的特征,那些波多黎各人聚居的社区与主流社区相互隔离,并且能够长期延续。
上海城市普遍存在的住房贫困心态,是一种延续时间长、波及面广的大众性心理,而并非居住条件最差的棚户区人群所独有。这种心态更多的是大都市住房资源紧张在大众心理层面的映射与回应,但这样的居住问题却不是上海这座城市所特有。我们今天仍然可以随时随地听到人们对买不起房子和蜗居生活的抱怨,他们将房子视为最贵的消费品,将房价与自己的工资收入相比,买房似乎是永远不能到达的彼岸。但实际买房困难者多为工作时间不长的年轻人(包括外地来沪的大学毕业生和新生代上海人),他们一时还没有足够的经济积累,或者是来上海打拼缺少一技之长的外来人口,这座城市可能不是最适合他们实现梦想的地方。
买不起房子,常常与过着拮据生活的年轻人的其他烦恼连在一起,也可以说是他们生活压力感的一个重要由头,因为衣食住行中毕竟房子最贵。这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从20世纪30年代之后,住房贫困的情结为何一直萦绕在上海民众的心头。在大都市快速发展的时期,任何一个非常态因素的出现都可能导致住房问题的进一步恶化,更何况上海一直处在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风口浪尖,经历着接二连三的社会动荡或者变革。直到今天,上海仍然继续着快速发展的节奏,住房问题仍然是政府和百姓关注的焦点。在人们抱怨住房难的同时,仍然可以经过若干年的奋斗和积累最终买到自己的房子,在这个城市定居下来,上海日复一日地迎接着源源不断到来的新人。再与世界上其他国际大都市的居住问题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上海房价的高昂很大程度上是国际大都市的共性问题,是城市强大吸引力的效应之一。如2013年2月18日《人民日报》以《忍受高房价,国外80后也蜗居》为题,报道了澳大利亚悉尼市的年轻人所面临的严重住房压力,而且日本、美国等国的年轻人也大多承受着无力买房的经济压力。
因此从历史的时间纬度和全球城市的空间纬度来看,自民国时期一直延续的上海市民的“住房贫困”情结,并不构成一种贫困文化,因为这种心态并不单单存在于某一类社区,没有明确的社区边界,具有这种心态的人群并不固定,它主要是由于这个城市的外来人口一直处于增长状态、而居住资源又一时难以匹配所导致的一种社会心理。
而作为底层人口最为集中的棚户区,似乎应当是与住房困难有关的种种负面心态(包括对未来改善的绝望)确定无疑地存在的地方,因为棚户区人口的贫困特征和与之相关的污名是显而易见的,不同时期的人们在表达对住房问题的不满时,都倾向于拿棚户区的景观和居住群体的生活状况作为靶子或者论据,但问题在于,贫困归贫困,但就住房条件的改善而言,棚户区群体本身对于未来是否抱有绝望心态?他们是否对融入城市社会丧失了信心?从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来看,答案是否定的。在1950年代初期,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加强棚户区的组织化,帮助棚户区群体融入城市发展的主流,为他们安排就业,提高他们受教育的机会,虽然历史形成的棚户区污名依然存在,但其社会影响和效应都得到了控制,像这样的情况是不利于形成贫困文化氛围的。政府通过各种舆论渠道和实际支持帮助棚户区人逐步建立社会责任感,提升他们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和期待,是帮助这一人口群体融入城市社会的有效手段。事实情况是,在建国后的十余年内,棚户区得到了城市政府的强化管理,基础设施和卫生环境得到统一的改进,确实呈现出与之前快速扩展时期更为整洁的景观样貌,棚户区人也积极参加到城市建设的各项工作中。尽管物质生活的贫困不见得有较大改观,但他们心理上建立了在城市扎根生活的希望,大部分棚户区人口拥有了当时上海人身份的标志——上海户口。在这样的情况下,以绝望感和边缘感为特征的贫困文化失去了孕育的土壤。
刘易斯对主流社会的制度因素在贫困文化形成中的作用有过深刻的分析:“贫困人口在主流社会的主要制度中缺乏有效参与或者整合,是贫困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个复杂的问题由多种因素所导致,包括缺少经济资源,居住隔离和歧视,恐惧、怀疑或冷漠,以及为解决问题所采取的权宜办法。”在上海棚户区的存在史上,贫困、污秽、污名都是客观的,但由于现代时期政府一直没有停止改善棚户区条件的努力,一直也将棚户区纳入城市规范管理之内,因此并未形成棚户区与周边社区和城市主流社会隔离的状况,更不存在像西方一些国家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相反,棚户区人口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还逐步迁往其他社区,形成新的居住格局,这些都有利于不同社会阶层的文化融合。但问题是,直到今天人们在表达对住房问题的不满时,为什么仍然倾向于拿棚户区作为靶子?这主要是由于历史延续下来的棚户区污名仍然有适宜生存的土壤,而污名主要又是棚户区以外的群体所施与的。
综上分析,上海城市社会普遍存在的“住房贫困”情结,虽然与棚户区的历史地理意象和污名有关,但却并未形成独立的城市亚文化,棚户区也并非贫困文化的滋生地,这是与其他国家棚户区或者贫民窟文化所不同的地方。■
[作者系星空体育·(china)官方网站历史系副教授,本文受到以下基金的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近代以来上海棚户区的历史地理与文化心态》(11FZS012);上海市哲社规划项目《上海城市化时期水网与聚落变化的空间过程研究(1843-2010)》(2011BLS005);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重点项目《开埠以来上海水乡景观蜕变的过程及人地关系研究》(12ZS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