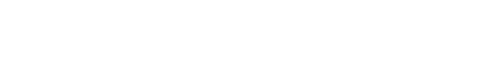江宏
从记事起就觉得父亲很忙。他的忙忙碌碌,年轻时,可能为名,稍长则要为利了;但却未得名,也没图到过多少利。或许是应了命书上说的“空忙”,可他忙得不亦乐乎,再空,只要乐在其中,空也就有了不空的意义。
对孩子的教育,因他的忙、被挤得很边缘。在我的印象里,父亲只对大哥上过心,甚至租架钢琴让他自小就有弹钢琴的美名(那时的钢琴是个稀罕物)。后来看到大哥在读大学时写的格律诗,平仄都合辙,定是得过“父之教”的。有诗为证,《醉歌寄儿辈》中道:“宁(大哥名)也堕地十五年,已习句读思雕镌。”可见是有教有育的;接着把我亮了相:“宏也跳踉类顽雀,乱鸦泼墨涂墙间。”放纵不是鞭长莫及,实固无心、无力。但“乱鸦泼墨涂墙间”,却是在父亲的默许下我童年放胆作画的真实情景,当时不会想到这竟是我绘画事业的起点。
童年的我,必是个名利之徒。因无利可图,利欲自然就消失了;但名欲的熏心却不论条件、不讲场合,得一个表扬,听几句好话,自豪感立刻升腾。有一技之长便等于可以占据长久的荣誉,于是,想当画家。当时纸很金贵,铅笔将正反面画得密密匝匝的,还不忍废去,再用毛笔画。不惟惜纸如金,而是纸贵如“金”,花钱去买,毕竟是在抢夺口中的零食。一直觊觎家里的白墙,想把它当纸用,终于忍不住动了手,毛笔蘸上墨写了“大跃进”三个字--这是个策略,谁敢反对大跃进?想因此圈下了一大块可以作画的地盘。正盘算着接下来怎么干,父亲开口了:“不要写字了,画画画吧!”可能是他不愿看满墙标语口号,更可能是对小孩正当兴趣的鼓励和支持。这个不费工夫得来的许可证,令我画兴激昂,不几天,满墙是画,找不到插笔的地方了,家人每天抬头低头都看着我的涂鸦。而没听到抱怨,不惜将破坏力来维护创造力,纵容兴趣,这也应算是“父之教”。
画出点名堂,有机会进了区少年宫美术组。我对水彩画的好感是易学见效快,而且成本低廉。一天,父亲给我一本上海人美出版的吴昌硕花卉册,令我爱不释手。其中一幅芙蓉花上题“粗枝大叶”四个字,长期在我脑中竖着,直到我透彻了中国画的精义后,恍然觉悟:这四字是写意花卉的要领。
因为这本册页,我爱上了中国画,一开始就跌入大写意的漩涡。我不知道父亲让我看吴昌硕的深意,可能是他更喜欢我弄中国的东西,但决不会以此来转移学水彩画的视线。父亲料我会追逐大写意的,真是知子莫如父,“父之教”于言、身之教外,又多了一重“引导之法”。
其实,父亲何尝不想自己的孩子有出息,他也有正儿八经课子的时候,只是由于根深蒂固的虎头蛇尾作风,总见开头而难闻续篇。
那年,父亲正专心致志地注着韩愈诗,心血来潮地要我读韩诗。第一首,韩愈的少年作品:“条山苍,河水黄。浪波沄沄去,松柏在山冈。”简明又具诗意,气势也阔大且朗朗上口,易读易记。怀着极大的兴趣等着第二课,父亲依然每天去上海图书馆的参考阅览室注他的韩诗,教读韩诗却再无下文了。可我一直记着这首诗,作画时每每题:少颂韩诗,此第一首也。不知情的,定认为我是读韩诗长大的。同样的遭遇还发生在孟子、墨子身上:认认真真地授完第一课,就悄无声息了。孟、墨的文章似云烟早已散去,倒是韩愈的那首小诗,在我心里扎下了根。前几年在晋南勾留,黄河边上仰望中条山,少年韩愈的诗竟与我意境相合,不觉感慨万分。这是我的“父之教”的一大特色:蜻蜓点水,轻盈地触动,短暂却入心弥久。
觉得自己的毛笔字写得可以题画补空时,我便学着做诗了,看王力的《诗词格律》,琢磨通今体诗的节奏,也未向精于此道的父亲请教。但我的歪诗经他略略改动后,竟有歪打正着的效能。举两个例子,题《红梅图》诗:“春来欲问梅消息,不用罗浮梦里寻,昨夜春风临小院,侵晨树树绽红心。”父亲将后两句改作:“试看东风临大地,枝头处处绽红心。”眼界抬高了,诗意也扩大了。题《水墨荷花图》:“水面出幺荷,跳珠急雨过;阵风拂暑气,留下清香多。”诗意平平,父亲也改了后两句:“风来吹不倒,为有墨香多。”彼时知识遭贬,父亲借题发挥,他说:有知,有识,才有胆气、生气,任凭风吹雨打,傲然挺立。如此的“父之教”,真是四两拨千斤,我也似乎明白了诗和诗意了。几年后,我在东北农村寄回一首词,词牌失记,可能是江乡子,也可能用了苏辙的韵:“秋寂寂,天际雁行斜,为问江南何所似,了应红了拒霜花。多少事,触处使人嗟,略把乡愁排遣尽,一瓯还品故乡茶,歌啸度年华。”竟获父亲的赞赏,说不改一字,入宋人集子也不逊色。我受宠若惊,惊得好几年不写诗填词。
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可我的“父之教”依稀可触可摸。金针度人,一生受用。
2015年元月于尚尚书屋
(江辛眉先生原为本院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