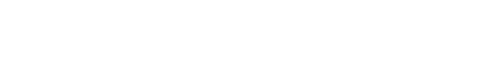作为特殊年代政治斗争中的舆论宣传与社会科学的实例,《学习与批判》对研究“文革”十年的政治历史、学术文化、新闻出版与知识分子,都是不可或缺的典型个案。

《学习与批判》1973年创刊,当年9月中旬上市。

《学习与批判》1976年第10期,这是该刊的最后一期。
1973年9月中旬,沪上书店与邮局开始发卖新创刊的《学习与批判》(以下简称《批判》)。虽然版权页上注明编辑部设在复旦大学内,但其实际组稿与编辑却出自当时上海市委写作组。创刊号《致读者》说,这是“一份哲学社会科学的综合性杂志”,似乎旨在区别当时同为上写作组操控的文学性杂志《朝霞》与自然科学类的《自然辩证法杂志》。这份月刊,出到1976年第10期,随着毛泽东去世而戛然终止。
尽管《批判》略具综合性文科杂志的外相,却决非学术性杂志,而是别有用心的政治刊物,记得当时圈子里还有过“小《红旗》”的自诩(《红旗》是当时的党刊,即今《求是》的前身)。不仅其创刊踏准了伟大领袖关于“批林批孔”的战略步点,在其后三年里,无论评论《水浒》运动还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都有过出彩的表现。
作为特殊年代政治斗争绑架舆论宣传与社会科学的实例,《批判》对研究前三十年中“文革”十年的政治历史、学术文化、新闻出版与知识分子,都是不可或缺的典型个案。时至今日,其创刊内幕究竟如何,命题定稿怎样运作,作者队伍如何罗致,杂志的执掌人物与主要作者在“文革”结束后有何遭际,在学术研究层面上都还不甚了然。倘有研究者结合对亲历者的采访与相关档案的调阅,申报哲社课题,倒真能填补空白的。
杂志许多文章都以化名登场,例如罗思鼎、石一歌、康立、石仑、翟青、任犊,但也颇有文章署以真名实姓,其中不乏当时与现今的海上学人。这些学人大体可分三种类型:一是当时已经卓然名家,二是当年已在学界但未享大名,三是其时尚未跨入学界而如今却已声名卓著。当然,第一、二类间有时难划定明确界限,只能以年龄段略作区分而已。
笔者当年无书可读,继创刊号后,大多购读过。去年从存书中检出,索性在孔夫子网上补齐所缺各期。今年恰是这份杂志创刊四十年,试就海上学人与这份杂志的因缘瓜葛,仅限文本,略作钩沉。囿于时间精力,未暇采访调查,难保史实有郢书燕说,学者或同名异人,亟盼亲历者赐正,更祈涉及者谅宥。
一
属于第一代的海上学人有刘大杰、郭绍虞、王运熙、顾易生、顾廷龙、谭其骧、陈旭麓、谷超豪等。作为学习体会,数学家谷超豪那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焕发出革命青春》(1976年1期),显然奉命配合当时“教育战线的大辩论”,不拟深论,其他学人之作颇值得一说。
刘大杰在《批判》上有四篇文章,依次是《读〈红与黑〉》(1975年1期)、《唐代社会与文学的发展》(1975年8期)、《李白的阶级地位与诗歌艺术》(1975年11期)与《韩愈与古文运动》(1976年4期)。就刊出篇数言,虽不算最多,在第一代名家中却拔得头筹。
刘大杰以治中国文学史著称,首发的却是外国文学书评,但他早年颇有关于欧洲文学史的论著行世,对此也就毋须怪讶。而强调《红与黑》复辟与反复辟的时代背景,也许才是这篇作品论的微言大义。其他三篇都是他1976年8月新版《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二册相关章节的先期发表。这部文学史自有特色,而以1962年版最得好评。据说,毛泽东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曾召见过刘大杰,“与他谈了四个钟头,主要就讨论文学史问题,对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里引述分析许多作家作品这一点,大加肯定”。“文革”爆发后,钦定保护的复旦四教授里就有刘大杰。他也得以奉旨改书,在1973年2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新版《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一册,荣膺彼时少有的恩典。由于毛泽东的青睐,批儒评法运动起来,江青“又要他以儒法斗争这条线为纲,来重新修改《中国文学发展史》”(见吴中杰《海上学人漫记》)。
据刘氏关门弟子林东海回忆,刘大杰其时“已完成一个修改稿”,全书“只是在某些问题上着以‘儒法’色彩,并没以此为纲”,他还将修改稿打印呈送毛泽东。1975年1月4日毛泽东告诉江青,“已印两部文学史,暇时可以一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十三册419页),一部就是这份修改稿的大字本。江青应该就在其后下懿旨的,还特赐他一部大字本。刘大杰回沪后,喜形于色地将赐书事张扬告人。应该与周一良同样,他认为江青“是主席的代言人”,“批林批孔也好,评法批儒也好,都是毛主席的部署”(《毕竟是书生》73页),便欣然从命。第一册修订本出在批儒评法前,尽管评孔子与《论语》已较前一版大相径庭,但尚未谬之千里。但1976年版的第二册就完全以儒法斗争为纲,而“武则天时期的文学”一节最是点睛之笔。
1975年8月3日刘大杰致信毛泽东,认为“韩愈以道统自居,鼓吹天命,固然要严加批判,但细读他的文章,发现其思想确有矛盾之处。如赞扬管仲、商鞅之功业等,都与儒家思想不合,而倾向于法家;他的散文技巧,语法合符规范,文字通畅流利,为柳宗元、刘禹锡所推许。对这些如果全盘加以否定,似非所宜”。次年2月12日,毛泽东覆信道:“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十三册522页)据揭载《韩愈与古文运动》的刊期推断,《批判》应是配合这份御批的。
“文革”一结束,刘大杰自然难逃谄媚江青的诟病,那部“文革”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也成为再批判的活靶子。批判者看不到大字本,依据的只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改写本,他“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一年后便黯然谢世,甚至没机会向公众说一声“毕竟是书生”式的自辩。
在《批判》上,郭绍虞刊出了《从汉代的儒法之争谈到王充的法家思想》(1973年4期)。他当时也在修改代表作《中国文学批评史》,他没有刘大杰蒙“旗手”垂青的幸运,却也是那种力图跟上形势的老辈学者。文章开头就表态:“我读了杨荣国同志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先后发表的几篇文章,非常同意他的意见,所以我在修改《文学批评史》讲到王充文论时,就准备特别加一章以说明王充思想的来源。”《论衡》在《隋书·经籍志》与《四库总目提要》都归入杂家,驳杂地涉及法家言论,自不足怪。但郭绍虞的结论却强调:“王充《论衡》恰恰充分地突出地表现了法家精神与法家思想”,紧跟色彩相当浓重。
郭绍虞的跟风似乎由来有自。据《海上学人漫记》:
大跃进年代,他根据当时流行的“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的理论修改他的批评史,出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这个修改本不能令人满意,宋以后的部分就没有再修改下去;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又根据儒法斗争的理论来修改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当然更加困难重重,终于没有能够出版,“四人帮”就被打倒了。
去世前一年,郭绍虞自编三卷本文集,有题记说:“现将我的写作汇编成集,区为三类:一为古典文学论集;二为语言文字论集;三为杂著(凡不能列入上述二类之零星诗文都纳其中)。三类或按写作年代,或按内容编次。其已见各种专著之中者,均删弃不列入。”但三卷《郭绍虞文集》都“删弃”了这篇文章。
王运熙、顾易生与李庆甲在创刊号上合署刊登了《试论屈原的尊法反儒思想》,顾易生、王运熙还有联名的《读洪皓〈江梅引〉》(1976年5期)。前文说屈原尊法反儒,自是趋时之作。关于后文,据葛剑雄的《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1975年5月,“因为北京大学写作组对《江梅引》(南宋洪皓所作词)的注释提出了意见,姚文元交给上海征求意见,由王运熙与顾易生负责,要他(指谭其骧)发表意见。”姚文元交办的任务,应是毛泽东晚年读大字注释本的需要。当时,文化部还抽调京昆名角、歌唱家与民乐演奏家,为其录制配乐演唱的古诗词,篇目应是毛泽东圈定的,其中就有《江梅引·忆江梅》(参见《毛泽东思想研究》1997年1期,胡长明《配乐古诗词与毛泽东的暮年生活》)。另据刘修明回忆,应毛泽东阅读之需,他与王守稼、吴乾兑以及复旦文史两系专家参加了大字本注释工作,接受的任务有“洪皓的《江梅引》(1975年3月21日布置)、姜夔的《梅花引》(1975年4月11日布置),就是毛泽东寻求精神寄托的产物”(《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2期,《从印制“大字本”古籍看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心态》)。
《读洪皓〈江梅引〉》主旨说,“《江梅引》从对梅的忆念、访问到爱慕、歌颂,以丰富多彩的画笔,描绘了精美而宽广的梅花图卷,反映了南宋时期爱国和投降两条路线的斗争。”其皮里阳秋也许在于强调“爱国和投降两条路线的斗争”,但其论述词的时代背景却未见改铸历史,即在今天,仍不失为站得住脚的文章。然而,他俩的总结性文集《王运熙文集》与《顾易生文史论集》都未将此文收入。顾易生晚年致友人信说:“自‘混入’复旦,长期在集体研究中混日子,亦有失有得。上面交的任务,风云变来变去,统稿改稿方面固然消耗了不少气力,做了许多无益之事。”(见《海上学人漫记》)这些“无益之事”或许也包括他在《批判》上的文章吧?
作为“文革”前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批判》上的文章是与弟子沈津联署的,题为《关于新发现的〈京本忠义传〉残页》(1975年12期)。沈津后在《学林往事》追忆其缘起:“1975年夏,我在一包明刻残页中偶然发现《京本忠义传》残页,仅存第十卷第十七页的下半页、第三十六页的下半页,并各残存前半页的后三行。次日,我即持残页请顾老、潘景郑先生审定,他们都认为此虽为残页,但不可小看,或许是《水浒》的一种早期刻本。后来顾老和我合作写了一篇《关于新发现的〈京本忠义传〉残叶》的文章。”当时全民评《水浒》正轰轰烈烈,短文结语也有一段关于“《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套话。2002年出版的《顾廷龙文集》收入这篇文章时,删去了与批《水浒》相关的卒章。这部文集以沈津始辑其师论著为基础编成的,其时他也已成为饮誉中美的目录版本学家。当年这段蛇足,不知出自顾老,还是沈津,抑或竟是编辑部的手笔。
中国近代史大家陈旭麓当时也在上海市委写作组,《批判》上有他的两篇文章。《“九州生气恃风雷”》(1975年2期)是《龚自珍全集》重印前言,议论酣畅,文采飞扬,是笔者当年读后的第一印象。文章也有时代的烙印,但总体思路应是作者思索所得。惟其如此,他在1982年有个改写稿,删去了几处强调龚自珍反法尊儒倾向的文句,几乎保留了基本结构与原有行文,改题《论龚自珍思想》,收入自编论文集《近代史思辨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他的另一篇《是拆庙还是补天——李贽与〈水浒〉及其他》(1976年2期),讨论李贽评《水浒》的思想倾向,文章发在全民评《水浒》的高潮中,难免有瓜田李下之嫌。其弟子编《陈旭麓文集》时,收录了前文而殳落了后文,应是经过斟酌的。
也许让人跌眼镜的是,《批判》上也有谭其骧的文章。这篇《碣石考》后收入作者审定的《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并在文末郑重括注“原载《学习与批判》,1976年第2期”,坦然表明其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据当年刊发此文的当事者回忆:
70年代初,我一直要谭先生给《学习与批判》写点文章,他一直拖着,到1975年他给了我一篇《碣石考》,写这篇文章的直接起因是1974年第二期《地理知识》上刊登了《沧海桑田话碣石》一文,论证了古代的碣石山确已沦亡入海。实际上谭先生要回答的是毛主席在《浪淘沙·北戴河》一词中写的“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的碣石山,究竟是不是在北戴河一带。他用大量事实证明秦皇、汉武、魏武所登临的碣石山就是现今河北昌黎北偏西十里那座碣石山。……他送给我这篇文章,我看了知道他的用意,看我有没有胆量发这一篇考证文章。我想了一下,毛泽东是一个诗人,他是从文学的视角去意会曹操《观沧海》那首诗的意境,当然不会去具体考证碣石山的位置究竟在哪里,他只能根据成说,如果说毛泽东同志在碣石山地点的论证上有误,也无损于他。所以我决定照发无误,但不张扬,太张扬了怕引起其他的猜测,那就不好办了。(朱永嘉《在求真中求是》,载《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对照《长水集》和《批判》两个文本的唯一不同,仅将“伟大领袖毛主席”改为“毛主席”,其他一字未改。一篇学术文章,历经乾坤翻覆,仍能基本不改毫无赧色地编入自己的文集,特殊时期的海上学人,也许唯有谭其骧庶几近之。

“文革”期间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成员合影

“石一歌”等写作组一般在丁香花园工作
二
在《批判》上发文的第二代学人,有徐缉熙、戴厚英、刘修明、余子道、吴乾兑、杨立强、金冲及、黄霖等。就刊发篇数看,徐缉熙有五篇之多,余子道二篇,其他诸人各仅一篇。
徐缉熙的文章中,点评当年沪上新诗的《读诗漫评》(1975年12期),只是应景之文,可以存而不论。毛泽东晚年再次号召读《红楼梦》,强调它是政治小说。徐缉熙的《论〈红楼梦〉》(1973年2期)、《鲁迅是怎样读〈红楼梦〉的》(1974年6期),应是配合这一号召而作。后文开篇就说“《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奉旨行文的痕迹一目了然。他的《漫谈看一点文学史》(1975年8期)说:“毛主席一再号召我们要关心上层建筑,要能文能武,提倡读一点历史,读一点小说”,兼之上年岁末毛泽东“已印两部文学史”,读一点文学史已成时髦。徐缉熙的文章自然是这一背景下的遵命之作,其论《水浒》说:这“是一部反映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尽管由于作者的阶级立场的限制,小说的思想倾向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以至颂扬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但这部小说仍有助于我们认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长处、弱点及其失败的历史教训”。文章写作与刊登时尚未获悉毛泽东有关于《水浒》评论的谈话,批判的调门还没高八度,总评与但书那几句话还不致太离谱。但毛泽东的谈话当月就以中央文件下发,次月4日《人民日报》刊发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于是,《批判》9月号登出《青年工人谈〈水浒〉》的座谈会发言时,特加一段《编者附言》,引用徐文上述论断后指出:“最近我们学习了毛主席的指示和鲁迅论《水浒》后,认识到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文章的作者在提高认识以后,对自己原来的观点进行了自我批评,并积极投入了战斗。”徐缉熙如何“自我批评”的,已不得其详,但时隔一月,《批判》就发表他的《歌颂什么,反对什么?》(1975年10期),副题是“评《水浒》的投降主义本质”,似乎旨在表明他的“自我批评”与“积极投入了战斗”。但这篇急就章颇有敷衍成文之感,远不及其评《红》之文畅达淋漓,也许他原就以红学见长,而急转弯的文章又不那么容易写。“文革”以后,《红楼梦》始终是徐缉熙学术重点所在。去年,他将历年“红学”成果,结集为《读红手记》,作品简介说他“文字不媚俗”。之所以能从奉旨评《红》到“不媚俗”,《后记》里有一句别有深意的话,道出了他对那段往事的深层思考:“当然,用现代的政治概念对这部小说作牵强附会的政治解读,更是伪科学!”
现以《金瓶梅》研究驰名的黄霖,在《批判》上刊出过《眼前二万里风雷》(1975年12期),是评新出《儒法斗争史话》的,“《史话》本身就是批林批孔的产物”,书评自然也是遵命之作。“编写这部近二十五万字《史话》的是十六名青年工人”,其中就有第三代海上学人,且留待下文再说。
戴厚英后以作家成名,“文革”前与“文革”中,也写评论文章。她的《“特种学者”的“考证癖”》(1974年6期),是批判胡适红学考证的。她后来反思说:那些都是脑袋还没有长在自己脖子上,作为别人的写作工具时所写的东西。包括这篇文章在内,她的那些东西都未收入其惨遭横死后行世的《戴厚英文集》。有学者指出,这些文章尽管对一般读者已无阅读价值,“对研究者来说,自然具有历史资料的意义”,“以后如有人编辑出版《戴厚英研究资料》,倒是应该收入她的理论文章的,因为这些文章毕竟反映出她青年时代的思想轨迹”(《海上学人漫记》)。善哉此言,推而广之,岂独戴厚英研究为然,对其他学者的个案研究也应如此处理。惟有这样,才能真实地还原学人的全貌,拼缀出有意无意被遮蔽的现代学术史真相。
1973年8月7日,《人民日报》奉命发表杨荣国的《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度的思想家》,拉开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序幕。《批判》不甘落后,为配合战略部署,也刊发了刘修明的《孔子传》(1973年2期)。笔者与作者曾有交往,可惜未便探询这篇文章的组稿秘辛(企盼他与这份杂志的所有亲历者,都能为这段历史留下足资采信的实录)。“文革”以后,他以治两汉史知名,相比代表作《从崩溃到中兴:两汉的历史转折》,由其主编的十六册《话说中国》图文本更享盛誉。
余子道的《从东北解放战争看林彪的右倾军事路线》(1974年6期)与《从抗战初期的战略转变看林彪的右倾军事路线》(1974年8期),都是批判林彪军事路线的。其时,批林是打死老虎,所谓“右倾军事路线”也是中央文件定下的调门,这样的文章在“文革”结束后也未必会受牵累。作为中国现代史专家,“文革”后,他出长过复旦大学历史系,其《民国军事史》课程颇有好评,他在《批判》上的文章倒都与这一方向有关。作为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中国近现代史学者,吴乾兑的《抗战时期的一本革命三字经》(1975年6期)虽有批判孔孟之道的套话,但介绍的是“红色文物”,想来其后也不致惹上麻烦。杨立强的《辛亥革命后的袁世凯》(1976年8期)发表之际,正值“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之时,尽管内容似无失实,但借袁世凯“疯狂复辟”牵扯到“翻案、复辟不得人心”(行文中这句话颇觉突兀,不知是否编辑部定稿时横插一杠),所指为何,明眼人一目了然,不知后来是否有“说清楚”的遭遇。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开设“北洋军阀研究”课程,文章的史实还能派上用场。
批林批孔方兴未艾之际,《批判》发表了金冲及的《〈天演论〉和中国近代反孔思潮》(1973年3期)。文章以毛泽东对严译《天演论》的评价“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为立论依据,勾画了一个“以反孔开始,以尊孔告终”的严复形象,而近代“新学与旧学、反孔与尊孔这两种思潮的斗争”则是全文大背景,配合批孔自不待言。改革开放后,金冲及曾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还出长过中国史学会,他不仅是中央文献出版社版《毛泽东传》的两主编之一,同时还主编了《刘少奇传》。由他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认为,1973年下半年毛泽东“没有主张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1680页),那么,他在《批判》上的“反孔与尊孔”之说,听从的究竟是哪家号令呢?二十世纪中国史,尤其后半期,也真让人云里雾里。
三
在《批判》上现身的第三代学人,除前文提及的沈津,还有杜恂诚、陈大康、仲富兰、胡申生、石源华与余秋雨等。除了沈津与余秋雨,大多数人当年还没跻身学界,只是以大学工农兵学员或“工人理论学习班”成员而初露头角。
杜恂诚当初还是上海味精厂工人,他的首发之文是《由“结合部”想到的》(1975年3期),歌颂在新的生产关系下,“哪里有结合部,哪里就有‘龙江精神’”。他还以工人身份发表了《“斗争并没有停止”》(1976年2期),评论“以第十次路线斗争(即毛泽东与林彪的较量)为背景”的剧本《樟树泉》(作者就是后来以《苍天在上》等官场小说三部曲而广受好评的小说家陆天明)。杜恂诚评《水浒》的文章都未署厂名。其《论晁盖》(1975年9期)以毛泽东“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为论旨,歌颂“晁盖毕竟不愧为农民起义的英雄”。他与“洪延青”联名发表了《宋江与武训》(1975年11期),也是配合领袖“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号召的,不得而知的是列名于前的“洪延青”究竟是化名,还是确有其人。“文革”以后,杜恂诚转入经济史学界,似乎远离了当年涉足的文史领域,近年《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上经常有他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大作。
陈大康先后刊有《论阮氏三兄弟》(1975年9期)与《并非小事》(1975年12期),后文说报刊文章难字注音的,与政治运动无关。前文首先论述阮氏三兄弟是“紧跟晁盖革命路线的革命将领”,而后指证他们在宋江那里“受到了越来越严重的排挤和打击”。文章虽也配合运动,但在六名水军头领排名次序上,以石碣上的天罡排序与数日后四寨水军头领排序相对比,考实宋江将三阮位置“在往后挪移”,却颇有说服力。他在“文革”后考入复旦大学数学系,后改投华东师范大学郭豫适的门下,专治中国小说史,以专著《明代小说史》而声名鹊起,抑不知《论阮氏三兄弟》在敦促其折回明代小说研究中占多大权重。
复旦大学历史系首届工农兵学员,1972年赴七一公社开门办学,参加了公社史的调查和编写。这册公社史出版当月,《批判》刊发了该校历史系学员王金保与石源华合署的书评《战斗的史篇》(1974年7期),副题就是“喜读《上海七一人民公社史》”。石源华其后留校,从事过民国外交史研究,现为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任,这篇书评不知是否其史学处女作。民俗学家仲富兰当年也是复旦大学工农兵学员,在评《水浒》时发表过《宋江的“反诗”》(1975年9期),现为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为培养所谓自己的“理论队伍”,上海市委写作组举办了历史学习班。据《青年工人讲儒法斗争史》(1974年7、8期连载)说:“这个学习班共有十六名学员,都是来自工厂和农场的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工人,主要是学习儒法斗争史。”该文就是“经过集体讨论,分头执笔写成的宣讲稿”,而上文提及的《儒法斗争史话》也是他们“几个月来的学习成果”。历史学习班成员在《批判》上列名可考的共九人,似乎唯有胡申生后来进入了学界。他当时是上海工具厂工人,除了参与编写上述宣讲稿,《批判》还选载过他与另两学员合署的《儒法斗争史话》之一《女皇帝武则天》(1975年1期)。江青曾一再把吕后、武则天捧为法家政治家,《批判》相中此文自有深意在焉,尽管作者也许未必了然。胡申生现为上海大学教授,作为知名的社会学者,在今年沪上“中国梦”主题群众性基层宣讲活动中还有他的身影。
在第三代学人中,余秋雨是最具话题性的。关于他与“文革”,与上海市委写作组,与《批判》《朝霞》等刊物,与石一歌化名等关系,早在本世纪初,就因“二余争论”而掀起过轩然大波(重要争论文章收入余开伟编《忏悔还是不忏悔》,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有人甚至揭秘他“写了一系列颇有影响的文章而深得头头们的欣赏”,乃至享受当时“中央首长”接见的殊荣(上引书108页)。笔者不想评断其他的是非,仅仅讨论《批判》上署其真名的大作。
据《余秋雨的一封公开信》(2000年1127期《文学报》),他说发表过《胡适传——五四前后》(1974年1期)与《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1975年8期,下称《读鲁》),而后特别声明:“在‘文革’期间,除了这两篇,我还写过两篇农村题材的散文。”两篇散文也许刊在《朝霞》上,此不具论。至于说只写过上述两篇大批判文章,却显然有误。仅在《批判》上,他的署名文章就有四篇,除以上两篇,还有《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对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1973年3期,署名秋雨)与《评胡适的〈水浒〉考证》(1975年10期,下称《评胡》)。
那封公开信提及《胡适传》说:“这样的文章对胡适先生当然是不公正的,但说当时产生多大影响,我不大相信。”前一句不失为反思;后一句却意在开脱,《批判》创刊号首印数高达三十万册,其后印数更有超过,说影响不大,过来人谁都“不大相信”的。对于《读鲁》,余秋雨承认是他“主动写的”,“但编辑部觉得太学术,在前前后后加了很多政治性的陈词滥调,这是当时惯例,但我由此决定不再在那里写文章。”或许那些“政治性的陈词滥调”并非他的手笔,但说“由此决定不再在那里写文章”却有悖于史实。
《读鲁》发表不久,《批判》就刊发他的《评胡》。该文劈头就说:“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投降派。他叛离五四新文化运动,投降过北洋军阀,投降过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相信作者仍会重复公开信里所说:“这对胡适先生当然是不公正的。”但有必要指出,《评胡》已以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1975年8月14日关于《水浒》评论的谈话,而这份谈话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到上海市委写作组,最早也在8月20日前后(详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十三册459-460页注释)。而刊登其《读鲁》的那期《批判》,据版权页,出版于8月18日,也就是说,其《评胡》只能写在《读鲁》发表之后。这样,他表白“由此决定不再在那里写文章”,自然陷入了罗生门。也许,公开信里那个说法,只是一时失忆而已。

1973年第3期的《学习与批判》发表了《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对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署名“秋雨”。
四
“文革”结束,在《批判》定性为帮刊后,深陷其中者受到了清查,由于当事者大多讳莫如深,其内情至今不甚清楚。本文涉及的海上学人中,第一代以刘大杰最为众矢之的,“他的罪名也不再是资产阶级学术观点,而是向政治上上纲上线了”(《海上学人漫记》)。陈旭麓回到华东师大,也遭遇了“风风雨雨,深文周纳”,“甚至连一个教授职称也历久不能解决”(唐振常《川上集·热泪祭旭麓》),多年位居“文革”后全国最资深副教授之一。另据2004年8月13日《新京报》的《余秋雨调查》,第二代学人中,徐缉熙也受到清查,“当时心里非常害怕,恨不得竹筒倒水,总希望早点解脱”。他还说及第三代学人余秋雨:“在文艺组肯定解脱得比较晚,我解脱时他还没有解脱。”据当今沪上一位资深的文史编辑(他实际上也应归入第三代学人)说,他当时还是工人,因在《批判》上发过三篇文章,原系统就长期将其打入另册。足见受《批判》之累者,远不止以上几位学人。
四十年后,之所以重新梳理海上学人与这份杂志的诸般关系,决非曝光旧闻,摊晒老账,而是旨在理性反思: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权力与学术、政治与学者、学术自由与学者人格、思想饥渴与文化禁锢之间有过怎样的异化,留下了哪些足资后人汲取的教训与启示。
首先,权力与学术的关系。现在知道,包括《批判》在内的那几份杂志,都隶属于当时上海市委写作组,而上海市委及其写作组又有着通天的关系,事后说有当政者直接操控这些刊物,也不为过。但当年批林批孔,评论《水浒》,乃至“批邓与反击右倾翻案风”,都以红头文件下达,这些当政者指示市委写作组(或工人学习班)的学人撰写批判文章,至少程序上都在行使最高指示与中央文件所赋予的权力。身处其中的一般学人有几个能够洞烛高层权斗的复杂内情,大都认定自己在为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当呐喊者,做马前卒。及至权斗定局、内幕揭晓,才知道站错了队,上错了船。就此而言,那些后来遭清查的海上学人,不啻是这种权力异化学术的牺牲品与受害者。即以徐缉熙两论《水浒》而言,前文已“左”,后文更“左”,但同样都是权力操纵学术的奉命之作。可以断言,海上学人在《批判》上的多数文章,都是权力支配下的产物。
痛定思痛,教训是沉痛的。学术之外的任何权力,不论以何种名义,走何种形式,都不应该役使学术;只有这样,学术才不会沦为权力的婢女,而权力执掌者的成败荣辱也不至于拖累学者的政治生命与学术生命。
其次,政治与学者的关系。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意识形态高度政治化,从批判《武训传》开始,经批判胡适与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反胡风事件,反右派运动,直至为“文革”揭幕的批《海瑞罢官》与“三家村”,政治运动几乎从未在学术文化界消停过。批林批孔与评论《水浒》,不过是其前那些披着学术文化华衮的政治运动登峰造极而已。在这类运动不断“洗脑”与威慑下,学者为了避免整肃与边缘化,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唯政治马首是瞻的思维定势与生存本能。郭绍虞文章的主动表态,顾廷龙短文的蛇足套语,乃至其他学人文章中那些“政治性的陈词滥调”,都不妨作如此观。
以今视昔,殷鉴是深刻的。那些以整人为目的的运动政治,是驱人于绝境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应该从学者头顶永远撤除,真正让学者研究学术,让学术回归学者;只有终结政治的绑架与政治运动的裹胁,学术才不会扮演政治的廉价吹鼓手,学者才不至于出于恐惧而充当政治运动的蹩脚传声筒。
再次,学术自由与学者人格的关系。在当年“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政治生态下,八亿人民全凭一个头脑在思考,一切以最高领袖的是非为是非。唯有谭其骧的《碣石考》,才配得上刊发此文的当事人日后的赞扬:“一以贯之的就是在求真中求是,在那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不屈从于任何权威,同时又能妥善地保全自己,在学术研究上要真正做到这一点也真不容易。”成为对照的是刘大杰,其晚年有诗自述知遇之情:“残生坚走红旗路,努力登攀答盛恩。”他的奉旨改书也自然出以旧士子仰答圣天子的报恩姿态,及至江青示意以儒法斗争为改书红线,在他看来懿旨一如圣旨,也就遵旨不违,照改不误。据其学生陈允吉说,对奉旨改书,他“在临终时感到十分痛苦和遗憾”。
回望前尘,启示是昭然的。就学者层面而言,一旦自我捐弃独立人格,自由精神也就无所附丽。即便在自由仍缺乏保障的大环境里,一个学人能否坚守价值观,在精神思想层面获得最大的自由,自身的人格修为还是占有相当权重的。只有这样,学者才能维护学术的价值与人格的尊严。就制度层面而言,应该进一步推动政治制度建设,确保每个学人都能享有“自由之思想”与“独立之精神”的最大空间,生产出独创性的精神思想,从而在中国形成迄今仍然短缺的思想市场。
最后,思想饥渴与文化禁锢的关系。十年浩劫,以“文化大革命”之名,行“文化大禁锢”之实。相信当时年当二十上下的过来人,都有同感,正处知识饥渴期却遭遇文化禁锢,最佳读书年龄却找不到书读。在这一背景下,先有批儒评法,后有评论《水浒》,在文化禁锢上开了一道窄缝,稍稍满足了求知欲。吊诡的是,这种打着学术幌子的全国性政治运动,却激发了一批年轻人的文史兴趣,无意中催生了现已成为中坚的第三代学人。但这代学人当年在思想上却呈现出“集体无意识”与“空洞现象”,自然易于接受当时宣传机器的政治鼓吹。也就是说,正当嗷嗷待哺多维新鲜的思想乳汁之际,喂给他们的却是一口狼奶。当时的政治运动以及包括《批判》在内为之摇旗呐喊的舆论书刊,输出的都是狼奶。笔者愿意坦承,当年读了《批判》上的《论曹操的尊法反儒》(1974年7期),对其论荀彧部分颇有自己的想法,便写了《试论荀彧的政治立场》试图参与讨论。后来考入大学选修魏晋南北朝史时加以改定,删去了昔日把荀彧说成是法家对立面的滥调,改题《略论荀彧》收入《学史帚稿》(黄山书社,2009年),并在自序里交待:“也算是立此存照,提醒自己:在学史起步之际,你也是喝过一口狼奶的。”
在无奶可喝时,被喂狼奶不是罪,苦于没比较,还会习惯狼奶的口味。在《批判》上发文的第三代学人,推而广之,现今文史学界五六十岁的这代学者,很少不受那口狼奶喂养的,但声名藉甚后,却少有承认自己是喝过狼奶的,有人还标榜“在那十年,我磨炼出了承受苦难、抵拒诱惑、反对伤害的独立人格”(《忏悔还是不忏悔》92页)。在那个年代里,除了像顾准、张志新那样的凤毛麟角者,恐怕少有人有资格自称已具独立人格(正是这种集体性的无独立人格,才累积成“文革”劫难的社会土壤)。在这点上,类似第二代学人戴厚英、徐缉熙那样的反思(朱维铮尽管没在《批判》上发过文章,生前却从不讳言曾是“罗思鼎”成员),倒是值得第三代学人尊重的。
反观在《批判》上亮相的三代海上学人,第一代大多老成凋谢,第二代也已基本退出学术舞台,第三代还活跃依旧,其中不乏文化精英与学界领军。对狼奶的反思,对狼奶型刊物的反思,推而广之,对那个特殊时代的反思,恐怕还是这些海上学人及其同代学者任重而道远的任务。唯有深刻地清算过去,反思历史,才能真正地启迪后人,不走老路。
(摘自:《东方早报》 2013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