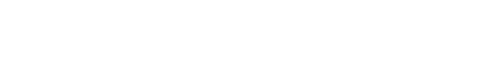作者﹕洪慶明﹐單位﹕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
法國大革命對現代世界至深至遠的影響﹐是留下了一整套觀念模式﹑行為儀式和革命術語﹐除“左派”“右派”“白色恐怖”之類耳熟能詳的政治話語外﹐還有“熱月”“霧月”“葡月”以及“旬日”等語匯。儘管後者祗是因為激蕩年代的重大事件且以之命名﹐才得以保留在今天的歷史課本中﹐但這些以拉丁語和希臘語為基礎創製出來的名詞﹐是1793年10月5日國民公會頒行的法蘭西共和歷各個月份的名稱﹐同樣屬於法國革命政治文化創造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它們超越了政治精英們以巴黎為中心的激烈爭鋒﹐在革命期間發揮著巨大的權力潛能﹐一度規約著幾乎所有法國人的日常生活節律。
法蘭西共和歷以1792年9月22日作為紀元元年﹐紀念共和國的誕生。它將每年分為12個月﹐每月30天﹐均分為三個“旬”﹐剩餘的天數放在年末﹐稱作“無套褲漢節”。像度量衡改革一樣﹐新歷採取十進制﹐每天分為10個小時﹐每小時100分鐘。這部新歷試圖按照理性的原則﹐按照大自然的律動﹐創造一種嚴整規則的時間體系。以後每年的新年﹐均以巴黎天文臺觀測到秋分到來的時刻作為開端。因為在這一天﹐如共和歷的首要設計者羅姆所說的﹕“太陽同時照亮兩極﹐繼而照亮整個地球。同一天﹐純潔通透的自由火炬﹐有史以來第一次閃耀在法蘭西民族上空﹐有朝一日﹐它必將照亮整個人類。”
從革命政治上來說﹐共和歷既是實踐的﹐也是象徵性的。首先﹐新歷不再以基督降生開始計算日期﹐抹去了各種各樣的宗教節日。時間的非宗教化﹐從日常實踐和想象方面承擔著去基督教化的任務。其次﹐18世紀的法國是一個地方差異極大的國度﹐農時﹑勞作習慣和宗教習俗的不同﹐使之存在著多樣的時間系統和時間觀念。“風俗﹑觀念和行為準則的一致性﹐毫無疑問會促成一個具有相同習慣和價值傾向的大共同體的形成”﹐因此﹐與度量衡改革一樣﹐新歷也是革命政權努力構建民族國家的有用工具。再次﹐新歷不僅僅是工具﹐它是有靈魂的﹐實體當中浸潤著豐富的意識形態內涵。新的紀元﹐象徵著神聖性從宗教轉移到歷史與政治﹔象徵著與時間的決裂﹕告別舊時代﹐走向新時代。共和國的誕生在其中成為歷史的零點時刻﹐已經埋葬的過去與革命許諾的美好未來在這裡截然分開。科學﹑理性﹑平等與自由就是新歷﹐同時也是它所計量的時間的靈魂。依然活在革命記憶圍困之中的史學家茹勒‧米什萊﹐在60年後談到共和歷時﹐依然充滿激情地呼喊﹐共和紀元是“正義紀元﹐真理的紀元﹐理性的紀元”﹐是“人類趨向成熟的紀元”﹗
如果將目光從政治維度轉向革命時代法國的社會﹐將時間概念植入社會史研究﹐考察計時體系與時間觀念對社會生活形態的塑造和規約﹐E.P.湯普森對工業資本主義時代有關時間與勞動紀律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有用的視角。法蘭西共和歷的功用﹐不僅僅是充當民族國家建構的工具和共和主義話語的容器。作為一種時間框架﹐它是國家與社會的接觸地帶﹐自上而下地滲透到社會領域﹐成為強有力的機制﹐形塑著日常生活模式乃至社會心理﹐其間充斥著強力﹑折中和對抗。
共和歷誕生之初﹐激進的革命派沒有意識到習俗和傳統的巨大慣性﹐並未通過立法方式要求所有公民遵循新歷的時間節律﹐將旬日而非星期日作為休息日。因此﹐在大多數地方﹐僅有政府部門﹑學校和地方激進團體實行新的時間表﹐集市和市場仍然按照傳統的日子開市或休市﹐農民和手工業者繼續過傳統的假日。一些地方政府﹑軍隊﹑特派員或雅各賓俱樂部地方分部強迫民眾遵循共和歷﹐甚至以“反對革命原則”的罪名懲處那些不過旬日節者﹐但即便如此亦收效甚微。
大恐怖時代﹐儘管在推行新歷中存在著立法上的不完備﹐執行上的不系統﹐但政府以強力姿態介入﹐試圖全面規範時間方面的事務﹐藉此將權力的觸角滲透入社會領域和確立社會秩序。“熱月政變”之後﹐失去了恐怖國家機器的支持﹐將新歷帶入法國人的日常生活的動力暫時地消失了﹐民眾迅速恢復了傳統的七天制時間表。共和歷受到大量的質疑和抨擊﹐國民公會議員朗熱內稱其為“暴君歷”﹐削弱了法國的生產﹐激怒人民反對政府。儘管恢復格里高利歷的呼聲很高﹐但在熱月黨人統治期間﹐共和歷卻延續了下來。其原因在於﹐正如法國史學家莫娜‧奧佐夫分析的﹐共和三年決定新歷命運的國民公會﹐雖然少了那些被推上斷頭臺的人﹐但仍然是相同的國民公會﹐共和主義的意識形態並未遽然中斷。
“採取最強有力的最具強制性的舉措強迫民眾遵循共和歷”﹐是取代熱月黨人的督政府統治期間的政策。共和五年果月18日政變﹐建立了相對左傾的政府﹐給共和歷重新注入了活力﹐強制執行旬日節成為優先目標。共和六年霜月14日﹐議員杜奧提出動議﹐呼籲確立國民假日﹐全體法國人都必須在“旬日”休息﹐禁止公民在公共場所工作﹐學校﹑集市和商店也須關門停業。該動議激起了大量的討論﹐並促使共和六年一系列相關法律的頒行。經濟與社會生活被迫按新歷的時間表重組﹐以共和歷的十天一旬制定集市和市場開市的日子﹐禁止報刊和公告等印刷品攜帶格里高利歷的日期﹐劇院和表演應該安排在旬日或國家假日裡﹐乃至結婚喜慶活動祗能放在旬日舉行。
共和六年這些有關時間的法令﹐是政府角色的極大擴展。按照米歇爾‧福柯的看法﹐在啟蒙自由主義話語的掩護下﹐調整權力機制規約社會個體的日常生活﹐是現代“規訓社會”興起的核心。但歷史表明﹐改造由風俗﹑習慣和文化心理構成的傳統地基﹐是場異常艱難的工程。民眾﹑官員的意願以及行政機器的有效性﹐是工程取得多大程度進展的關鍵。民眾對革命和宗教情感的強弱﹐地區和城鄉之間管控程度的差異﹐是影響共和歷採用的重要因素。在諾爾省﹐政府下令商舖在旬日必須關門歇業﹐不准擺售產品﹐禁止木工和瓦工在公開場所勞作﹐違令者將遭逮捕和罰款。這些舉措看上去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督政府的專員向巴黎報告﹐旬日在本省較大的城鎮得到了遵守。
然而﹐傳統習俗和心理﹐民眾基於日常生活的理性計算﹐是法令政策一時難以改變的﹐導致政策的執行效果時常流于表面。商舖雖然在旬日關門﹐但他們利用法律的“漏洞”在店內繼續工作﹐並且故意弄出很大的聲響。不獨如此﹐公然的犯禁也層出不窮。在一個名叫奧博丹的小小教區裡﹐僅共和七年葡月的一個月時間裡﹐就報告了144起違反禁令的行為。在工商業城市裡昂﹐政府密探報告﹐共和歷極少得到遵守﹐集市和市場仍然遵循舊例。在該密探看來﹐共和歷漫長的工作周制度以及對星期日的宗教虔誠﹐是造成此種情形的主要原因。農村地區的情況更差﹐農民利用法律條文中有關“急迫情況”的規定﹐聲言田地裡的農活急切需要做﹐在播種和收穫季節﹐在守禮拜日的同時﹐公然在旬日勞動。地方政府官員在向中央呈送的報告裡﹐經常抱怨由於民眾的“偏見﹑愚昧和習慣”﹐使共和歷遭到忽視﹐形同虛設。洛埃-加龍省的官員說﹐是“習慣以及鄉村當中團結協作的需要”﹐而非宗教偏見﹐阻礙了旬日節的成功。榮納省甚至發生群眾騷亂和起義﹐反對新歷﹐捍衛傳統的基督教時間。反抗的話語也緊跟形勢﹐以捍衛人民主權和宗教自由的革命原則為口號。
從共和六年到共和八年的兩年多時間裡﹐共和歷及其界定的時間框架在政府與社會的博弈中﹐失敗多於成功﹐走過了它的“輝煌”歲月。共和八年霧月18日(1799年)政變﹐是共和歷命運的又一個轉折點。到1806年1月1日被廢除﹐這最後六年“無疑是它的衰落史”。它為法國人規定的時間節律和意義﹐在此期間陸續遭到了拋棄。
共和歷在法國社會的實踐歷程表明﹐歷史猶如滾滾流動的長江大河﹐其表面看上去變化萬千﹐浪花不時飛濺﹐但沉寂的底部﹐日復一日靜靜流淌﹐穩定連續﹐是決定歷史走向的強大基礎。任何一種政治理想﹐祗要與千百年來積澱下來的社會日常實踐存在脫節甚或衝突﹐那麼這種理想在踐行中必然遭遇重重阻礙乃至歸于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