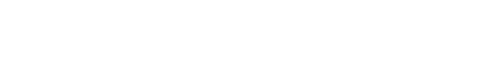时间:2017年10月13日 来源:文汇报 文/畔叶千明 译/尹禄
19世纪,沙俄传道团的成员在北京学会了汉语,他们对中国进行探索,关注宫殿、城市和人们的状态,并向本国报告,或者在沙俄的刊物上发表相关的研究文章。他们在西方汉学家群体的影响下写作,但同时认为自己的活动和西方汉学家相比更加富有成效。
引言
世界各国在自己文化的启蒙时代都或多或少受到了中国经典文本的影响,俄罗斯也不例外。19世纪上半叶,受到西欧社会思想影响的俄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接受了西欧关于“天朝中国”的阐释,同时也开始关注本国****用俄语完成的关于中国的著述。
在现代语文学的发展过程中,19世纪的俄国社会是逐渐形成关于中国问题的想象与对于中国文化的态度的,特别是在历史哲学领域。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文化对于19世纪俄国的影响,这方面问题至今仍未获得充分的研究。19世纪上半叶,俄国传道团曾积极研究过中国文化,本文正是着眼于这一点,进一步阐释俄国传教士对于中国经典文本的研究。
北京的俄国传道团以博学广识著称,而传教士也不单单从事宗教活动。按照中国朝廷的看法,沙俄传道团与其说是宗教组织,不如说是清朝和邻国文化交流体系的一部分。与其他俄国和西方传教组织的一个不同是,传道团成员住在北京的一座教会会馆,即“会同馆”,后更名为“俄罗斯南馆”。
19世纪传道团的成员在北京学会了汉语,他们对中国进行探索,关注宫殿、城市和人们的状态,并向本国报告,或者在俄国的刊物上发表相关的研究文章。他们在西方汉学家群体的影响下写作,但同时认为自己的活动和西方汉学家相比更加富有成效。这些人的文章证实了他们的远见,但文章也不可避免地有着某些局限性。
如何学习汉语
俄罗斯的中国研究始于俄国传道团,所以他们对中国经典文本的研究也必定发端于那个时期。德明是第十一届传道团的一名学生,1830至1836年旅居北京。德明的文章《中国行》(1843)里就提到了他们着手研究中国的原因:
而且,为了摆脱最艰难的境况,不再当一个会说话的哑巴,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为自己找一位中文老师。
对他来说,在异国他乡学习语言不只是一项任务,同时也是生活所需。
之前的传教士(第十届传道团的成员)给我们推荐了一位已经教过他们五年的被贬职的中国官员——佟先生。
我们的老师……一开始就以无与伦比的灵巧和令人叹服的漂亮书法征服了我们。写完第一页,他大声地朗诵了一遍写下来的字,然后让我们跟着他读出每一个字……但是,最有趣的是我们开始上课的时候,是一个汉字都不认识的,而我们的老师也不懂俄语,他用汉语给我们解释他写的字的意思。我们的中国老师竭尽全力,大汗淋漓地教,我们大汗淋漓地听他讲,不停地翻查汉语词典,最后,至少和开始的时候相比,我们做到了!当然,之前传教士留下的笔记也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的语言课程每天都持续两个小时左右……在老师的帮助下,过了半年我们差不多学会跟老师和中国人交流了,两年之后我们就进入了汉语博大精深的神秘国度,四年之后我们甚至已经能够自如地谈论抽象事物了。
在其他资料中,他更加具体地描述了学习汉语的过程:因为想要学起来容易些,他开始读简化版的中国百科全书——《三字经》,这本书是汉学家雅金甫推荐的。读完《三字经》之后再阅读中国名作《四书》的时候,课程进行就顺利多了。德明写道,他觉得研习这本书是一种责任,因为“几乎没有一篇文章的表达是陌生的”。在《三字经》里就有关于小孩子是如何开始学习的内容:小学终/至四书/论语者/二十篇。
在北京的俄罗斯人不能自由地出入使馆的生活圈子,所以很少有机会和中国人交流。雅金甫描写了和中国平民交流的障碍:“我对他很好奇,但他却说‘官老爷不让我和你们说话’”。雅金甫在学习汉语的时候,还研究了经典文本,尤其是儒家学说。奇怪的是,雅金甫没有描述他们是如何学习满语和蒙语的,而很多传道团成员应该是学会了这两种语言的。
俄罗斯东方学家,尤其是雅金甫,对西方人眼里中国的形象持强烈的批判态度。
出人意料的是,我的切身感受证明,如果旅行者对所到国言语不通,那么他大概会不可免俗地产生有失公允的评判。
通过研究经典文本来学习语言——这是天主教传教士们,特别是耶稣会会士们推荐的方法。事实上,依照西方传教士的方法来发展中国研究,“能避免错误”。这个方法就是:注意力集中在经典文本的研究上。
按照原定计划,我的旅行日记是要记录在北京的生活内容的。然而,过了几年,当我已经收集了一些汉语资料之后,我在这些记录里发现了很多不准确的地方。因此,我被迫删掉了一些看法,那些众所周知的观点不一定都是对的,有一些推测甚至十分可笑,我也抛弃了这些根据片面观察或者偏见得出的浮于表面的结论。但是,这些修改也让我的日记变得形式单一,了无生趣了。
传道团成员的分裂
曾在1805—1806年间作为尤·阿·格罗夫金(1762—1846)大使来华使团成员的费·费·维吉里(1786—1856)写过,他为什么加入来华使团。
科学并没有对我产生深刻影响,它没能迫使我踏上遥远的旅途,甚至也不是看见新国度的好奇的原因,我周围的俄罗斯现代人中没有人到过那个国家:相比之下我对去德国的兴趣更大,经济上的极度拮据才是我所能承认的促使我决定开始这两年流浪生活的原因。
该时期的俄罗斯贵族和学者对西方有着极度的迷恋,对于这些人来说,东正教教堂和他们完全没有关联。说到格罗夫金,正如维吉里写的那样,格罗夫金大使本人出生在瑞士,是基督教信徒:“当他出现在叶卡捷琳娜的宫殿里时,他身上除了名字,没有任何俄罗斯的特质。”
第九期传道团首领阿波罗斯就曾在格罗夫金的使团被孤立,维吉里写道:
我们很少,或者说几乎看不到大司祭的修士们和学生们,我们的高级官员并不是非常敬畏东正教,格罗夫金是宗教改革派信徒,波多茨基是天主教信徒,而巴伊科夫没有任何信仰倾向。我很为阿波罗斯感到遗憾:他还不到二十五岁,对于尘世来说,他还是个年轻人,从来没有走出过宗教学院的高墙……他进入这个混乱且不严肃的大使馆是一件多么不幸的事情啊!据说,在我走之后他也没有惹过任何麻烦……
最后,格罗夫金把阿波罗斯从传教团首领的位置上撤掉了(之后,格罗夫金上书建议将首领换为雅金甫,这在下文将要说明——笔者注)。
如上所说,近一半的传道团成员为非宗教人士,所以教职人员与非宗教人士经常陷入分裂状态中。德明作为第十一期传道团的成员,就像上文提到的,见证了修士们和传道团的疏远——所以阿波罗斯也就不是个例了。
传教士们、大部分神职人员,还有对事物持自我观点的非宗教人士,他们通晓非宗教的语言,但是他们的所思所感都不可能也不应该和非宗教人士的一样:我可以在他们那里得到建议,但却得不到支持。
可能,传教士们缺少和非宗教人士一样的公共教育履历,这直接导致了他们彼此很难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北京的俄国传道团几乎很难在中国人中间从事传道事业。
一位“无神论者”的汉学研究
而传道团成员中所谓的世俗观点和思想与今天理解的“世俗”是同一个意义吗? 我并不这么认为,我们继续看雅金甫的例子。他继任第九期传道团的首领之后,成功地成为最优秀的汉学家。
雅金甫,也就是尼·亚·比丘林(1777—1853),是杰出的汉学家,他确立了当时汉学研究的方向,苏联的中国历史传记作家彼·叶·斯卡奇科夫认为,那个时代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比丘林时期”。与此同时,雅金甫自认为是“非宗教修士”,甚至还自称为“无神论者”。他因为回到圣彼得堡之后不去教堂而被剥夺职位,受到米·巴·阿列克谢耶夫的文章《普希金与中国》的影响,他还打算在1831年左右退出修道院生活。文中阿列克谢耶夫这样写道:
尼古拉·马林诺夫斯基的拉丁文日记中最有趣的一部分是关于雅金甫的内容,按照马林诺夫斯基的说法,这位非宗教修士因为主教的申诉而被委派到了瓦拉姆斯基修道院,取名谢拉菲姆,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他并不认为基督比孔子更伟大”,并且对永生的灵魂表示质疑。
尼古拉·马林诺夫斯基(1799—1865)是一位波兰历史学家。后来阿列克谢耶夫没有继续深究这一问题,而是为了阐释雅金甫的思想,把这一部分内容用作了材料。在1837年,当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被刊登发表的时候,“无神论者”无疑广受好评。因为本人的水平有限,无法仔细探究马林诺夫斯基的思想和这本拉丁文日记的细节。但是,我们无论如何要尝试着看,哪怕是阿列克谢耶夫评论的一个小片段——取自1828年1月30日的日记内容:
雅金甫谈了关于中国女性的事情,他对于宗教和信仰问题完全持开明的态度,也很喜欢吃肉。他觉得,基督教的开创者一点都不比孔子更伟大。他尽管并不否认,却很可能是反对永生的。
他跟马林诺夫斯基谈起过,修士一定或多或少是非宗教人士,但也可以说,各种各样的宗教活动至少是吸引他的,而且他“声明不否认永生”。他不是东正教保守主义者,但他对宗教和信仰的观点却比无神论者更加复杂。
令人好奇的是,在这一段中他把中国的儒家学说和欧洲基督教作对比,这让我们想起了西方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会员们的文章。研究者已经指出,他在自己的文章中称儒家学说为“宗教”。这种观点从中国第一批基督教传教士开始就普遍流传,后蔓延至整个欧洲。
儒家学说的实质一如既往地吸引着所有人的关注,这些人试图区分中华文化和其他国家文化(尤其是基督教)的异同。儒家文化的形成有着极为复杂的根基,包括:(1)崇拜、形式、观点、信仰和源于上古时代的神话学形式;(2)礼节和仪式,它们是国家统一和稳固的标志;(3)哲学概念,它们由孔子及其弟子提出;(4)民间礼仪、迷信、节庆,包括日历中的节日。可见,儒家学说——它是一种复杂多面的现象,其实质不可能用三言两语轻易概括出来。
换言之,儒家学说的不同定义反映了对它的不同理解。另外,雅金甫的定义之所以值得关注,还由于在现代的中国研究中,儒家学说根本不属于宗教。
传播形式:《太极图说》的翻译(1832)
虽然雅金甫翻译了很多儒家学说的资料,他却只发表了其中的《太极图说(宇宙起源形式或生命与精神规则的发端)》和《通书》。其余的译介,例如《书经》,他并未发表,至少没有以书籍的形式发表。《太极图说》的译作修正版被翻印为《中国、其居民、风俗、习惯和教育》一书第十一章《宇宙存在体系述解》。彼·尼·斯卡奇科夫曾经写道,在《中国考古出土手稿》目录中有一份名为《天文志》的手稿。如果这份手稿是“起源论”的早期版本,那么可以推测,雅金甫是在旅居北京期间接触《太极图说》的。为了更深入地探究,则必须要确定雅金甫使用的中文版本。对于这本译著,我们仍需继续研究。
现在,我要提及的一个词是“通”:雅金甫把它翻译为“参透/渗透进内部”。
在行动和静止的情况下,他(圣人)领悟了个人的起源和华夏进程,在最为广阔和固定的范围内作用在他自身,并渗透进入他的精神内部。
“渗透”与朱熹和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理念有关:能参透所有的人可以被称之为“圣人”。
参透这个概念,在雅金甫对中国民众教育的理解中起着重要作用。
“儒学”这种宗教的内部机理是建立在纯哲学起源基础之上的,而且是那种通过学院教育渗透进入所有社会阶层的哲学,就像是水渗入海绵一样。
“阶层”指的不仅是社会等级,也包括不同的宗教团体:“中国三个宗教派别的人员:和尚、道士和喇嘛,在举行宗教仪式及与父母的关系方面,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着装规范。”
总结
雅金甫(比丘林)诠释了作为宗教的儒家学说,他认为重要的是,儒家学说比其他宗教形式更高级,它还渗透进了民众的内部精神世界。雅金甫(比丘林)对儒家学说的这种观点为沙俄传道团研究中国经典传统和他翻译经典文本时的独特选择奠定了基础。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儒家学说不含唯灵论的一面凸显时,它并不能被界定为宗教:儒家学说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基本理论,在它之上还存在着真正的大众宗教。正如19世纪俄罗斯杰出的传教士汉学家巴拉第神父在一封信里所指出的:“儒家学说的实证主义……为任何体系的构建保留了广阔的空间。”
(作者为东京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