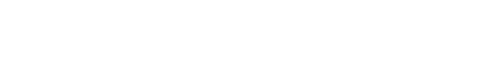作者:日本京都大学西洋文学院教授 中村唯史 译/田洪敏
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天地彼此交叉融合的观点在1960年代的苏联作品中并非特例。在这些故事中准确地传递了一个我们习惯称之为“苏联文学”的语言与思想特征,它是隐藏于苏联文学中的一种暗流。
尤里·卡扎科夫(Юрий Казаков,1927—1982)是苏联1960年代著名的抒情散文作家,其写作风格简洁、明晰而优美。1970到1980年代,他的作品《十二月里的两人》《蓝色的和绿色的》和其他短篇小说经常成为日本俄语课堂的读本。
这些短篇小说里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擅于抒情而细腻地描写城市年轻人的精神世界。同时,卡扎科夫的自然随笔也独具特色,特别是对于俄罗斯北方自然风光的叙写。如果谈及苏联文学中描摹自然的作家,卡扎科夫应该是与普里什文和帕乌斯托夫斯基比肩的。可惜的是,他年纪尚轻就去世了,在人生的“暮年”,他的作品也很少出版。
在本文中,笔者打算简要分析一下卡扎科夫或许不那么有名的、写给孩子读的一个故事《红鸟》(1963)。《红鸟》是好的故事,但非精品。尽管如此,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故事中准确地传递了一个我们习惯称之为“苏联文学”的语言与思想特征。这种语言与思想特征是隐藏于苏联文学中的一种暗流,通过分析这部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种暗流。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叫米沙的小男孩儿。他和祖母住在一起,他的父母到远东去了,自然,是去工作了。米沙很快就到了上学的年龄,他的父母给他寄来了校服、书包和铅笔盒等等。他焦急地等待着去学校的日子。及至9月,米沙发现自己的班级里没有一个自己熟悉的小伙伴,老师教的那些他早都知道的字母也令他厌烦。他决定不去学校了,白天就在自己的破烂家里瞎玩儿或者等小伙伴们放学了和他们在街上耍。他蛮喜欢这种日子,直到有一天老师阿列克谢·巴甫洛维奇来家访——是个个头儿很高的年轻人,只是他的一只胳膊有点歪斜,脸上还有一道深深的伤疤。
米沙问老师疤痕的事情,巴甫洛维奇说自己原来是个极地飞行员,开雅克飞机,比如邮政飞行,会驾驶飞机去接紧急的病人,在海里搜寻渔夫等等。有一次,他在飞行中受了重伤,被迫中止了飞行员生涯。
巴甫洛维奇邀请米沙到自己家来,他拼装了不少塑料滑翔机。他给米沙看自己的作品,两个人决定去试试刚刚拼装好的一架红色的滑翔机。他们来到河边高坡处试飞,一开始滑翔机晃来晃去,还不稳,后来借助气流,终于飞离了小河的上空,越飞越高。
在这篇小故事中,应该关注作家对于景色与空间的描写。我们已经谈及,卡扎科夫是自然描写大师,而在《红鸟》这个小故事里,风景描写是彼此相连的,成为这个故事内部最重要的有机部分。比如辍学后,米沙眼中的自然是这样的:
漫长的夏天过去了,秋天到了。公园里的树叶又开始落了,又能看见大苹果了。肥鹅在湿漉漉的草地上蹒跚。总是下雨,雨后湿乎乎的草地好像变成红色了,而草却还是绿的。丫头们和小伙伴们从森林里拖出来一桶桶的蘑菇。干嘛要学习呢,——米沙想着,——如果可以简单地活着?非得上学才知道草会生长,需要修剪,然后秋天叶子会变黄?才会知道大雁和仙鹤会飞过河那边的田野?才会知道白桦林里会长着“白桦树牛肝菌”?才会知道杨树下会长着“杨树牛肝菌”吗?
辍学后的米沙沉浸在自我封闭的世界里,而老师巴甫洛维奇来家访并且向他展示了一个丰富、宽广的世界。
峡谷那边是森林,森林变成金黄色了,黑土地上落满了白桦树叶。而天空却是蔚蓝色的,简直不像是秋天的感觉。阿列克谢·巴甫洛维奇和米沙来到河岸,河水汩汩流淌,岸边的柳树却似细细的银条,河的那一侧,越过树林里的小土丘,就看到了一片片田地。地里都是卷心菜和土豆,社员们已经开始收割了。甚至能够从高处看到卡车,看见姑娘们红色或者是绿色的围巾,和成堆的收下来的卷心菜。
上面两段引文都是在写秋天,是的,但还是有区别的。前面是写孩子们采摘野蘑菇;后一段则是社员们在秋收,但是换一个角度看,可以说无论是哪一种情形,人们都生活在与大自然的和谐当中。《红鸟》并非读者通常认为的“成长小说”:一个沉浸在自我世界的小男孩儿在老师的感召之下走向了人群。果真若此,那么在米沙眼中的前后风景就应该是有区别的了。而故事中的米沙眼中的风景和社员秋收的风景是同一不可分割的空间。
拓宽视角来看,《红鸟》中的空间并非仅仅限于上述的风景描写。故事的题目是“红鸟”——指的是飞向天空的滑翔机,在米沙的想象中,滑翔机甚至可以到达宇宙。作为成年人的巴甫洛维奇不打算破坏孩子的想象力:在回答米沙滑翔机能否飞很远,并且飞向太阳的时候,他巧妙地将话题引向了航天之父齐奥尔科夫斯基。
这里,故事内部的空间突然就指向了宇宙。指向了齐奥尔科夫斯基,一个发明家,而且他就是生活在我们州的人,这里读者大概会猜到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俄罗斯梁赞地区(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家乡)——看来米沙渴望的宇宙并非多么遥不可及、多么神秘的空间,而是一个人类在未来可以期待的空间。
呼应齐奥尔科夫斯基的观点,在《红鸟》中并非存在一个不可预知的空间,而是一个可以和太空相互延展的地球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孩子们可以采摘蘑菇,社员可以收割庄稼。笔者还注意到,在米沙与巴甫洛维奇的谈话里,无论是滑翔机还是火箭,都采用了拟人的方式——都在飞翔,人工滑翔机也好,甚至小蜘蛛也好,世界并没有断裂,世界上的一切都以同一种方式存在,按照老师的解释,一切都在飞翔:米沙,我的兄弟,我们的生命,鸟儿们,火箭,甚至地球本身,就算是太阳也都在飞翔。
《红鸟》的结尾表达了世界连续性的特点:九月,一切都浸在的阳光里,风吹过大地,轻柔而温暖。在河对岸,田地里,人们看见了滑翔机,他们用手挡着光线,在指缝间看见这只“红色的鸟”,看着它像一个神奇的飞行物一样越飞越高。而滑翔机越飞越远,虽然米沙和阿列克谢还留在岸边,可是他们好像也一起飞起来,和滑翔机一起环顾大地,为今天的日子感到快乐——人们在田野里和谐地劳作,可是人们发现了他们的滑翔机。这里的滑翔机和故事主人公是彼此呼应的。地上的人看到的是无限上升的空间,而宇宙则对于地球上的人充满慈爱,一切都很和谐。如果用一个图示来表示大体如下:
《红鸟》这个小故事发表的时候正是苏联在太空领域占得先机的时候,但是《红鸟》并非是简单的胜利者的颂歌:小说中的太空也并非是人类征服或者服从的对象,太空只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延续。它似乎很愿意等待并且邀请人类来做客。当然,《红鸟》也不是简单的集体农庄的颂歌:米沙自我封闭的世界、老师阿列克谢、农庄的田野、天空或者是宇宙,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正如上面简图所示,这个故事中存在三个彼此关联的层次。阿列克谢、滑翔机和米沙趋向于向上,响应天空的邀请;天空释放阳光和九月的和风;而地上的人儿则追踪着可以飞翔的一切;而和滑翔机一起渴望太空的米沙和阿列克谢则看着地上的和平的人。三个层次彼此叠加与渗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红鸟》的世界是一个独立的整体。
而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天地彼此交叉融合的观点在1960年代的苏联作品中并非特例。著名苏联阿瓦尔族诗人拉苏尔·卡姆扎托夫(1923—2003)在1965年前后完成的诗歌《鹤群》,后由马克·别尔赫斯谱曲传唱。这首诗歌中逝去的战士变成了鹤群,而在大地上的人们则感受到和他们是一个整体。
我有时候觉得,
没有从前线归来的战友,
不是在那时已被埋入土地,
而是变成了白色的鹤群。
他们从旧时飞来,
飞翔,向我们低鸣,
真的不是因为,
我们经常仰望天空吗?
静默、悲伤地仰望天空?
诗歌的结构是逝去的战士,化作白色鹤群,从天空向地上的生命呼唤,而活下来的人听到逝者的声音,抬头仰望天空。是的,诗歌的结尾,对于如此抒情的“我”来说,还是回归到了战士的死是不可避免和挽回的:“终有一天我会加入到这鹤群,/我也会飞翔在这灰色的烟雾中,/在苍穹下像鸟儿低鸣,/呼唤着你们,留在这片土地的人们。”——万物的规则本也是逝者飞于天空,生者立于土地,当他们在某个时候彼此对视的时候——世界也就是永恒。
类似的母题和形象是这一代人的写作特征之一。在苏联形成了自己的“我”,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弗·维索茨基(1938—1980),这位行吟诗人的歌曲中得到表现,如1969年的《他没有从战场中归来》。在这首歌的第五节:我下意识喊了一声“朋友,来抽根烟吧”,可是回答我的却是静默。这里,死者与生者好像是一个人。接下来“逝去的人不会留我们于苦痛”,虽然活着的人并没有感受到这一点:倒下的人就像是哨兵守护着我们,在接下来的诗节中这种生者与死者的关系转变成为天空与大地的关系:天空映入森林,如同映在水中,而蓝色的树则静静矗立。这里天空代表着已经逝去的战友,而代表着生命的森林却染上了天空的蔚蓝色。
1960年代的《鹤群》和维索茨基的《他没有从战场上回来》,无论是作为诗歌还是歌曲都广为流行,这些作品中的天空与大地彼此凝视,天空是死亡,大地是生命。所以可以说,死亡与生命本也是彼此对视的。因为生死的关系恰好是记忆的命题,在这些诗歌当中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不仅仅是空间意义的,也在于它的时间视阈。
卡姆扎托夫的《鹤群》、维索茨基的《他没有从战场上归来》都是俄罗斯民族性的人格化表达,可以在里面找到清晰、一致的主题、结构甚或是世界观。这种共通性已经超越了语言和民族的界限,不仅仅停留在1960到1970年代。
我们认为,苏联文学中关于世界一体性的思想是延续了白银时代的文化遗产,这其中包括索洛维约夫的思想,也包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柏格森的影响。如果考虑到20世纪现代性问题,这一问题不仅存在于苏联文学当中,在日本及其他国家的文学中也有体现,这完全可以建构一个新的文学研究视角,这种分析不应该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