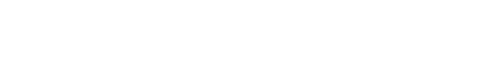小编的话 风吹在脸上,还有阵阵寒意,但阳光洒满了整个墓地。

詹丹
清明时节,想起了几处墓地。
去年,我本有两次出访的安排,一次去俄罗斯社会科学院普希金之家,还有一次是日本神奈川大学。但因为患病多年的母亲状况已不太乐观,就推掉了日本会议,匆匆去了趟俄罗斯。除开与普希金之家的专家会谈外,我和几位同事也参观了俄罗斯的几个艺术博物馆,但印象最深的,却是莫斯科郊外的两处墓地。一处是新圣女公墓,墓地管理员是一位大学退职教师,学识渊博,带我们边看边介绍,墓地里有各种风格迥异的雕塑,切合墓主人的身份,也体现出雕塑家们独具匠心的理解。我看到了政治家赫鲁晓夫、葛罗米柯的墓;看到了艺术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梁赞诺夫的墓,看到了作家果戈理、契诃夫的墓,也看到了巴别尔、法捷耶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墓,甚至看到了青年英雄卓娅和舒拉的墓。几乎是一部小型的俄罗斯包括前苏联的社会名人史。我拍下了舒拉墓碑前的圆雕,一个头微微向上仰起、做着跳跃姿势的青年造型,也拍下了靠着大理石垫背像是已经瘫痪在床的奥斯特洛夫斯基浮雕。我想把这些照片通过微信传给病床前的母亲看,我知道母亲曾经喜欢其中的某些作家,但踌躇之下又放弃了,因为毕竟这是墓地,对一个病重的老人来说,也许是忌讳的。所以,当我去了图拉的托尔斯泰庄园,当我拍下托翁的坟墓:一个没有墓碑、没有雕塑的坟墓,一个只覆盖着绿枝、被穿透林荫的阳光所照亮的坟墓,一个被茨威格称为世上最美的坟墓时,我也没有把照片传给母亲。
后来,在我回国的2个月后,在2016年的10月下旬,母亲因镇痛麻药用过量,突然去世了。
我们遵照她生前与红十字会签下的意向书,把母亲的遗体捐给了复旦医学院。许多年前,当我父亲去世时,他的遗体也是捐给医学院的。

前几年,在青浦福寿园,墓区专门辟出一块地方,把捐献者的名字刻在碑石上,红十字会每年也会举办一些纪念活动,邀请愿意捐献自己遗体的人及其家属前往。我曾连续两年接到通知,但都因为要陪护患病的母亲而没能参加。
2017年3月1日,是红十字会的遗体捐献日。我第一次去福寿园参加纪念活动。那里景色迷人,墓区里也有不少雕塑,依稀有新圣女公墓的影子。在竖立着捐献者名录碑石的区域,我在1983年的一栏里,找到了父亲的姓名,又在另一块2016年的碑石上,找到了母亲的名字。我突然感到有些遗憾,我觉得我应该带母亲生前来看看这里的,哪怕是推着轮椅也应该过来。我应该让她知道,她以后安息的地方,景色是那么迷人,有那么多对死亡的意义理解相同的人,互相陪伴着。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先走了那么多年的我的父亲。虽然我清楚,这里没有捐献者的墓葬,但我仍然愿意把这里视为是他们最后的安息地。
我走出这片区域,沿着道路往大门走时,无意中看到了紧挨着路边的一块墓碑上有我熟悉的一个名字,她是东方广播电台一个女主持,我曾经还和她合作过一档节目。墓碑上有她的照片,她的样子是那么甜美,一如她的声音,充满了滋润心田的力量。

是的,20年前,我和她合作广播台的一档深夜播出的“博士谈名著”节目,先期录制,每周3次,每次半小时,围绕一部名著,先讨论20分钟后,再由她朗读10分钟的名著片断。本来只要我设计几个问题,她提问我回答,再朗读我勾出的几个片断就可以了。但她十分认真,总要求我提前一两个星期把书寄给她,她要从头至尾读一遍,写下疑问的地方,再来一起讨论设计的问题。每次播出时,我,还有我的母亲,都会等到深夜,一起听播出的效果。如果我出差了,我母亲还会把播出的内容录下,让我回来听。我劝她早睡,说这节目是给晚上失眠者听的,她没必要这么等、等这么晚的,我母亲总微笑着说,真喜欢听那位主持者朗读。我说,难道我的讲解就不好吗?母亲又笑着说,你怎么能和她比?话虽然说得有些扫兴,但我心里是认同母亲的说法的,因为每次我听她的朗读,总觉得我之前的讲解,是多么苍白无力。我甚至想,后来这档节目突然停办,也许是我的讲解太没有人气的缘故。所以,后来过去许多年,我在上海图书馆听王安忆小说讲座时恰好碰到她,结束时,她把我介绍给陪她来听讲座的广播台的同事,说我们以前一起合作做节目,我都觉得有点难为情。但即使这样,也不能因此说我母亲就不想听我的讲解。还记得,我在广播电台讲了一阵名著后,我母亲退休的单位通过她联系到我,要我去他们单位,在周末职工学习的时候也讲讲名著。我大概讲了2小时,在一片掌声中走下讲台,这才发现,母亲从一个角落站起,满脸通红,向我迎上来……
我呆呆地望着主持人墓碑上的照片,突然想,如果母亲去世前就来过这片墓地,知道她安息的地方,与她爱听的那位朗读者,挨得这么近,对她来说,是不是也是一种安慰呢?但是,这已经不可能了。而且,以前,我也没有想到过告诉那位主持,我的母亲,还有我,曾经那么喜欢听她的名著朗读……
三月初的上午,虽然风吹在脸上,还有阵阵寒意,但阳光已经洒满了整个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