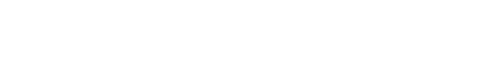地方院校还能再出郑克鲁这样的大家吗?
陈恒|星空体育·(china)官方网站世界史系教授
时间转瞬即逝,一眨眼,郑克鲁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今天这个会议既是对先生的追思会,亦是先生的学术思想研讨会,更是中国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界的一次盛会。大家看看出席会议的嘉宾名单,可以说是群贤毕至。这是星空体育·(china)官方网站的荣耀,也是中国外国文学界的高光时刻。
今天来宾很多,我尽量在简短的时间内表达我的敬意。郑先生一生著述4000万字,不仅是法国文学翻译的守望者,更是伟大的学者和教育家。一所地方师范大学,能有这样的学术大师,放在今天学科评估的背景下,似乎是匪夷所思的;郑克鲁先生以一人之力,翻译如此多法国文学作品,这在当代学术界是无法想象的;他在一所地方高校,几十年如一日,培养了一代代致力于文化交流与文化批评的学者,这是令人难以企及的;他在中法文化交流、乃至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取得如此骄人成绩,更可谓是空前绝后。基于以上四点原因,我愿将郑先生身上体现的这种成就与意外,称为中国学术界的“郑克鲁现象”。如果这个命题成立的话,按着这个思路,我个人感觉有这样几个问题需要认真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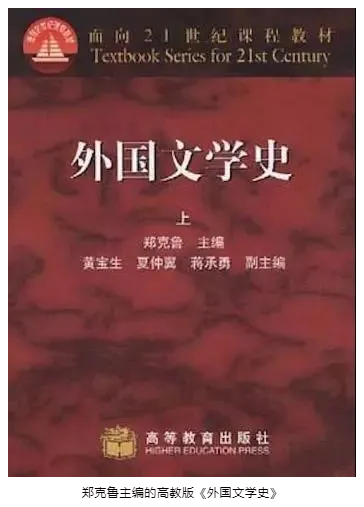
郑克鲁主编的高教版《外国文学史》
第一,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我个人感觉,可能在郑先生之后,地方高校很难再出现像他这样的翻译家、学术家和教育家。但愿我的感觉是错误的。我印象中,郑先生1987年来到上师大直至去世,那时他47岁,正是一个人文学者富于创造力的阶段,可以说把人生中最重要的、最好的学术年华都奉献给了上师大。就其学术成就而言,按照今天教育部和大多数高校的治校思路,郑先生早已被其他更好的学校高薪聘走。如果所有的学术精英都集中在双一流高校,那地方大学、地方高等教育便越来越差,难道这是国家的幸事吗?
第二个问题是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科?我们如何看待人文学术研究的意义?今天拿到的会议手册,第一页郑先生的这句话给我触动非常大:“生命就是你给世界留下了什么”。这也让我想到另外一句话,1936年浙江大学的竺可桢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第一,你来做什么?第二,你毕业以后做什么样的人?郑先生用实际行动回答了竺可桢校长的提问。教育就是让人尽量成为全面的人、完善的人,多留给世界一点东西。而文科教育就是为学生提供人文批判思维、培育情感认知,让学生不忘价值与美感,郑先生的话就是他对价值的体悟。这是当下正在倡导的新文科教育需要认真思考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如何看待域外文明?这是我们特别要关注的,因为异质文化永远处于对流之中,唯其如此,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才能被其他文明不断激活,从而不断抓住发展和完善的机遇。任何文化若想弘扬自身的价值观,都要正视人类所有的文明成就,都要借鉴其他民族的创造发明,都要与当代世界各国进行合作互动,而非将自我隔绝于世界,贬低乃至否认别人的成就。以开放的心态欣赏域外文明,以严谨的方法探讨别人取得成就的内在机制与深层原因等等,这都是当代域外文化研究的使命,更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人总得有一点情怀,尤其人文领域的学者,学术界本应该为社会提供安身立命的精神食粮,现在也功利化了。像郑先生这样,几十年甘于坐也乐于坐冷板凳的学者,几十年精心翻译法国文学、培养学生的学者,似乎不多了。

郑先生低调豁达,他的性格是宽容的,从不与人相争;他对待中西文化交流也是宽容的,在翻译研究法国文学的同时,不忘回顾东方文学。人与人之间要包容,相互尊重、相互学习,文化之间是这样,国与国之间也一样。理想的社会既要讲效率,也要讲公平,更要讲一点真善美。说到这里,想到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说的一段话,愿与大家分享:
关于人类当代状况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当代状况既是过去发展的结果,又显示了未来的种种可能性。一方面,我们看到了衰落和毁灭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真正的人的生活就要开始的可能性。但是,在这两种互相矛盾的可能性之间,前景尚不分明。
老师们、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努力为未来一切存在的可能性进行切实可行的工作。像郑先生这样,少说一些大话,多做一些实事,兢兢业业为世界做点什么,争取为世界留下点什么。谢谢大家!

链接地址:https://mp.weixin.qq.com/s/xU45dRzdvVTNXW1p6B4Bd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