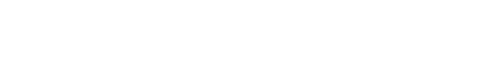凡人任钧
陈伯通
“笔会”去年11月8日刊发王尔龄《追怀任钧先生》一文,读后心有所动,想起自己和任钧先生的一些交往。
我与先生相识于1958年夏。那时,上海师范学院(现上海师大前身)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刚组建,他从上海音乐学院调入,我从人民解放军转业而来。
其实,“任钧”这名字在此之前早已印在我脑中。“当祖国需要的时候,\我们马上拿起枪,\跨过鸭绿江,\卫国保家乡……”这首激越高亢,让人热血沸腾的歌曲,在上世纪50年代,曾响遍中华大地,感召过无数青年投入抗美援朝。其词作者就是诗人任钧。记得五十年代初,我在华中师范大学就读,诗人曾卓给我们授课,讲到三十年诗歌时,也多次介绍任钧先生充满激情的战歌,和“诗歌是时代的旗帜,是炸弹”的诗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曾卓老师还对任钧先生与杨骚等成立“中国诗歌会”,以及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时参与“太阳社”的文学活动,给予了积极评价。
现在,我一向景仰的任钧先生出现在我面前,竟是我的同事,还是同乡,同是广东梅州客家人,怎不让人特别高兴呢!
那时,先生年近半百,中等身材,不胖不瘦,风度优雅;板刷式头发黑白相间;双眼皮眼睛,明亮有神;面色红润,泛着光泽。
按分工,任钧先生负责俄罗斯苏联文学的教学,朱雯教授负责西方文学。当时,“向老教师学习”的气氛特别浓厚,我多次随堂听先生讲课。先生的讲课很有特色,广式普通话,字音清晰,声情并茂,教学方法灵活多样。他不照本宣科,眼睛总是望着学生,与学生眼神交流,气氛活跃。譬如,讲到普希金时,他自己朗诵《纪念碑》,而《致西伯利亚囚徒》、《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等,则让学生推派普通话特棒的同学表情朗诵,先生作出点评。其他如莱蒙托夫的《帆》、涅克拉索夫的《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片断,以至高尔基《母亲》中尼洛芙娜在法庭上的演说,都通过朗诵,加深了学生对作品的理解与记忆,提升了思想情操。这也许就是作为诗人的任钧先生的最爱吧,因为诗歌原本就是供人朗诵的嘛。先生授课十分专注投入,在剖析马雅可夫斯基长诗《列宁》时,他会情不自禁模仿列宁发表演说时的英姿,把手指向前方,引得学生脉脉而视,啧啧称赞。
“文革”后,已近古稀之年的先生,又调入校文学研究所,撰写了多篇回忆文坛逸事文章,发表在《中国新文学史料》上,为新时期文学事业作出贡献。
与任钧先生相处几十年,留给我永不磨灭的印象是先生性格恬淡平和,乐于助人,见到总是笑眯眯的。
初相识时,先生曾问起我住哪儿,上海有无亲人。我说:“初来乍到,举目无亲。住学校东部琴房(原上海音乐学院教学琴房)。”先生随即不假思索地说:“那以后就常到我家坐坐。”
据我所知,从解放后到先生去世,几十年里他先后在虹口横浜桥、徐汇衡山路和湖南路一带房舍住过。有的环境嘈杂,有的楼梯狭窄,房间都不大,陈设简朴,但收拾得非常整洁。每次上门拜访,他总是笑眯眯对我说:“不错吧!我对生活的要求不多,知足常乐。”
初冬一日,先生突然出现在我住宿的琴房里,看到五平方米的房间,单人床、写字台、竹书架、靠背椅四件家具就把房间塞得满满,一只衣服箱也只能放床下。我介绍说,这是学校免费提供的,就连水电费也全免。像你一样,我也很知足。先生笑眯眯地说:“很好,很好,知足就好。”先生又随手掀起床单,见只有一张薄薄的稻草垫,便说:“我们广东人怕冷,过几天我给你带些棉花票,到漕河泾去买张棉垫。”先生比我整整长一辈,慈父般随意自然而真挚的话语,立时让我备感温暖;同时也让我想起他常对我说的: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文革”初,先生遭批判,打入牛棚,监督劳动,扫厕所。一天,我们偶遇校道上,交谈了几句。忽然,一个身影闪过,定睛一看,原来是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的姚蓬子先生(姚文元父亲)。姚先生臂戴红色“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袖章,朝中文系资料室走去。我知道,那里有以他为首的“劲松战斗队”,写过许多大字报。我嘀咕了一句:“他有靠山,儿子在中央文革,不但不用进牛棚,还能参加造反派。”任钧先生马上极其严肃,小声说:“你胡说些什么。别管这么多,管好自己。”好一个“管好自己”!记着先生的告诫,我洁身自好,才比较平安地度过了那黑暗的年代。“文革”结束,拨乱反正,教师们谈起当年的派别斗争,有人问我参加了哪一派,不待我言,任钧先生抢先不无幽默地说:“他吗,参加的是‘逍革会’。”大伙儿纳闷:“是上海市的消防队革命委员会吗?不可思议。”先生连声说:“他什么也没有参加,是逍遥派。你们大串联,打派仗,他回家抱孩子哪。”引来了一阵笑声。
1989年秋,我妻英年早逝。已是八十高龄的先生得知后,从湖南路赶到桂林路上海师大家属区宿舍,十分艰难地走上五楼我家,神情悲戚,把一束白花放在我妻遗像前,三鞠躬,转身用粤语劝慰呜咽不断的我的年迈岳母。随后,他走近写字台,在纸上写下“同命鸟 卢嘉文(任钧先生原名)”六字,纸上留有两滴泪水。见我不解,他便细声说:“古人说,人生三大不幸是:幼年丧父,中年丧偶,老年失子。前两项,我和你都经历了。保重!”我无言以对,唯有泪如雨下。告辞时,先生还不忘叮嘱我那从英国读书回来的独生女儿:“照顾好爸爸。”我搀扶先生缓步走下楼,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又不禁泪如雨下,回到家大哭了一场。
先生的最后几年,因脊椎病,行动不便,在养老院度过。
如今,先生如一朵雅云升天而去。以上所写的记忆碎片,是我无法忘记的。它将继续在我脑中拼接,显示出清晰而又完整的图像:任钧先生是一位充满爱意的凡人。
摘自《文汇报》